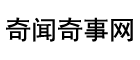迄今为止,学界的主流意见,仍将孟子视为一个“民本”论者,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否定了这一看法。
《孟子》收与齐宣王田辟疆的对话,凡十四处。“有恒产者有恒心”一语,将人民失掉人的常性、常情(“恒心”)的原因,归结为其财产的缺乏与无法保障(“恒产”),可谓千古名论。但与之同样震撼人心者,如《梁惠王》中有关国家如何辨用贤才一段,却因种种原因,鲜为后人理解: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如不得已”,绝非后来所说勉强或迫不得已,而恰恰是说,国君以“为天下得才”为“不能容已”之赏心乐事;进退生杀的把柄,也既不操之在己,亦不在左右亲宠或朝中重臣,而唯在“国人”之手。只有经过“国人”公断为贤、为不可、为可杀,然后加以察考,果然与其论相符,才能再加以进退。
然而,“国人”是什么意思?谁是“国人”?
孟子
一般都把“国人”解为一国之人或国中各色人等,“国人皆曰”遂被说成是“民意”或“社会舆情”。换言之,“国人皆曰”,也不过是听听民间呼声,了解下民意、民情罢了,故从来少有人瞩目于此。但台湾孟学名家黄俊杰先生却指出,“国人”是一个在春秋时代有“与闻国政权力”的“社会政治群体”;他们以在野之“民意代表”的身份,内可决定国家大政,外可影响合战大局。黄先生的判断,不仅有孟子文本以及周边文献如《左传》《国语》的证据,并有杜正胜《周代城邦》等有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名着为之佐证,绝非故作惊人之语。故其论述,不仅足以使这一段脱胎换骨,实也足以令孟子对“人民权利”的论述,为之一新。
然而,迄今为止,学界的主流意见,仍将孟子视为一个“民本”论者,以为“民贵”之论与后世哀民、悯农之抗辞并无二致,不过是天下本为民享(for the people)、民有(of the people),对于强调人民治(by the people)之权利观念与制度形式,则绝未梦见。实际上,在并不知晓“国人”的相关研究的情形下,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已通过对“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及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详尽研究,否定了这一看法。
但,不仅徐先生当年的诘难久已石沉大海,杜正胜、黄俊杰等人的研究,也少有人知。深究其因,笼罩文化民族主义阴影之下的种种“文明特殊论”妄断,不能不再次引起我们的警觉。其实,并非只有雅典,才存在民治的独特实践。撩开“帝国”的帷幔,就足以看到轴心时期文明的真正方向。幸运的是,《孟子》留下了足够多供我们探询的线索。
孟子有一个不易觉察的证明:“使有菽粟如(有)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易得,故人都乐以助人而不虞其匮乏。如使人无饮食之忧,有“恒产”之保障,又何需忧有不仁者?是对匮乏的忧惧,才使民铤而走险,丧失其仁。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求难避易?不使之在消除其匮乏之虞的同时,复苏其仁,却反而要以此为凭,厚诬其不具备参与政治的道德能力(按一些人对“恒心”的解释)?或只有关入道德理想国的“笼子”,成为严明的礼法治下的婴儿呢?
但水火-菽粟之论证的成功,却不能停留于传统的“仓廪足而知荣辱”的解释。孟子不仅不会承认人是经济动物,且一再疾言,人在“饱食、暖衣、逸居”的“无教”状态中,同样可能使恒心放失,“近于禽兽”。《滕文公》中更直接提出了他的“教民”之论:“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我们知道,这完全足以使孟子落入“家长政治”的指责。但其后“教之”所及的内容,却由一身而达于家、国、天下,正是《大学》所论修、齐、治、平的公共治理范围。难道“恒心”之维持,竟然也如对水火菽粟的需要一样,需要权利的建立与推展吗?
事实正是如此。《梁惠王上》论恒产恒心的着名段落中,紧接“百亩之田”的即是:“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矣……”“庠序”为三代学制,“教民、养民”之义,确定无疑,都是预为人民参与公共的基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对前举“国人皆曰”的例子,加以深思,以明确其主张人民参与公共治理的“自然权利”的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