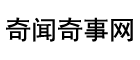1941年,宁波城沦陷。
那时新江桥还是浮桥,日本兵开始于此设岗,中国人但凡路过,都必须向他们90度鞠躬行礼。
1943年,13岁的王景行被迫辍学,开始在一家“参糖”店当学徒。一天,去旗杆巷47号的傅家送货,结果发现来接东西的,竟是个日本女人,40来岁,穿着和服,踏着木屐,说着咿咿呀呀的日语,看上去很是阔气。而她身后那栋漂亮的二层洋房里,却不断传来中国女人惊悚的惨叫。那声音实在太过凄厉,以至于时隔70多年,他还时常想起。
有人告诉他,那里是慰安所,是日本鬼子寻欢作乐的地方。
那一年,慈溪姑娘小杨也只有13岁。母亲说,外头兵荒马乱,她就听话地躲在家里,一心想着多纺些棉纱,好买身好看的衣裳。可不曾想,10月的一天,家里也闯进了日本兵,3个人凶神恶煞,一下子把她推倒在地……
她还那么小,对于发生的一切似懂非懂,只觉得自己好像被生生劈开两半,直到日本兵走远了,下身还在汩汩地流着鲜血,怎么也止不住,疼到她都以为自己快死了。
可她活了下来,在大人们讳莫如深的眼神里,听到有人说:自己被轮奸了……女孩的余生都活在此事的阴影下,结婚三次,婚变两次,晚年无比凄凉。
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市抗日战争期间遭到日军性侵犯的妇女共计1547人,其中“慰安妇”309人。多数在战争结束前就已遭日军杀戮,或者被迫害而亡。至于那些含恨活着的少数人,也是面容模糊地隐藏在人群中,十年间仅找到3人,目前幸存者不详。
我希望她们还在,又希望她们已安眠。
522份口述里的秘密
如果你也曾亲眼看过这份由浙江省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耗时十年方才完成的《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宁波犯下的性侵犯罪行调研报告》,就会知道什么叫“罄竹难书”。
1941年4月20日,日军占领宁波
从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镇海第二次登陆,到1945年9月15日侵华日军在宁波投降,4年零5个月里,日军在宁波犯下了大量的性侵犯罪行。对此,日军慈溪联络官芝原平三郎居然在半浦(现属江北区慈城镇)的乡镇长会议上这样无耻地强辩:“我士兵的强奸妇女实是没法的事,他们离开家乡已经六七年了。”
由于在抗日战争期间及战后国民政府开展的全国性战争损失调查中,并未将各地妇女受强暴的情况专门加以调查,许多当事人也不愿将被日军强暴之事公诸于众,现有的数据统计,显然远远少于实际。比如海曙区,“慰安所”有两处,但调查出的“慰安妇”仅为10人,明显偏少。又如,余姚作为日军侵略的重灾区,在94名性侵犯受害者中,查出有名有姓的仅4人,明显不足。实际受害者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1939年5月遭日机轰炸后的宁波主要街道
十年间,市委党史研究室共收集到522份口述资料,仅有3份为受害者本人陈述。故事开头的小杨就是勇敢站出来的其中之一。余下的两个,一位是象山县新桥镇海台村的张奶奶。1943年春天,日军进犯海台村,31岁的她同另外6个妇女躲于一间柴草屋内,不幸被搜出,遭到强奸。
另一位就是令所有人印象深刻的余奶奶。直到今天,提起她,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专家胡国忠依旧有些激动。“那个奉化的老太太,曾是慰安妇,我们找到她的时候,身上还留有80多个伤疤,那是日本人用火烛活活烫出来的。”余奶奶记得,被抓的那天是1942年农历三月初五,惨遭强奸后,她被押到了村庄附近的金紫庙,从前她总觉得那里的菩萨最灵,所以常带儿子过去。可那一天,她却被扒光衣服倒挂在那里,当着公婆、儿子还有菩萨的面,被日军用拜神的火烛烫出一个又一个恐怖的伤口。因为没有上药,那些伤口总是结痂后烂开,烂开后又再次结痂,皮囊千疮百孔,心里的伤也是一辈子都没有好过。
她们的故事,还只是日军对宁波所犯罪行的冰山一角。
她们在人间,见过地狱
在1547位受害者中,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最大的年逾六十。其中多数都被折磨致死。在奉化市社会调查到的70位受害者中,被强奸致死的就有18人。
抗战期间宁波市遭日军性侵犯妇女人数统计表
1942年5月15日中午,宁海县长洋村郭某之妻惨遭20余名日军轮奸。次日,含恨而死。这也是目前宁波发现的针对单个妇女实施性侵犯日军人数最多的案例。
1941年4月,在宁波市西门口,日军拦住一对母子,兽性大发,先用刺刀刺进小孩的肛门将其举起来,后当众对眼睁睁看着孩子惨死的母亲实施强奸,并将其刺死。
1945年7月,一名齐姓的年轻妇人,被象山石浦日本警备队抓走。日本兵说她是中国兵的“暗探”,将其轮奸凌辱,最后用木棍刺入阴部,弃尸路上。
对于不从者,日军手段更是毒辣,据庄桥姚家村孙文菊老人回忆,1941年日军进村,那个与她相识的女孩孙小妹抵死不从,结果被割下双乳致死。
……
日军设在奉化的慰安所
至于那309位慰安妇,更是长期过着非人的生活:她们被关在暗无天日的慰安所里,平日禁止穿内裤,就为方便日军随时随地、不分场合老幼,疯狂地实施性暴力。一个慰安妇一天甚至要“安慰”几十名士兵。当中如果有人怀孕,就强制流产。
同中国所有慰安妇一样,她们中有不少人都丧失了生育能力,甚至落得终身残疾。死,反倒成了另一种解脱。
“当时,因为我年纪小,不来月经,所以来糟蹋我的日本兵从没断过。”
“为了早点出来,见到两个弟弟,后来我就依他们的做,要我怎样我就怎样,我这样讨好他们让他们满意,就是想他们能早一天放我出来。可他们根本不会放我。”
“我的身体实在是熬不住了,姐妹们就对我说:‘你快逃吧,这样子下去你会被弄死在这里的。’”
……
人间地狱,不过如此。
而那些没有被凌虐致死的女人,也没活着走出炼狱。
抗日战争结束后,“慰安妇”的噩梦仍未结束。
据说,一位从前住在桃渡路的妇人,从慰安所出来后,数十年来离群索居,鲜少与人接触,靠摆茶摊和卖木莲冻为生,最后孤独终老。日军投降后,为数最多的奉化“慰安所”的妇女也大多去向不明,只知道有2名妇女嫁到西圃村,但都无法生育。
可悲的是,在日本的《广辞苑》上,对她们的备注居然是:“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
她们瑟缩在穷乡僻壤中苟延残喘。有人握着刀,害怕的夜夜不敢入眠。
“他们(日本政府)什么时候赔罪?我能等到那一天吗?”没有答案。
309位慰安妇一年少过一年。
其余的,虽然没有成为慰安妇,却也因遭受性侵犯,或死或残。有人疯了,也有人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今天,也无人知晓,山间的沟沟壑壑里,哪一座是她们的孤坟。
……
那些施暴的日本兵,那些还活着的当年施暴的日本兵,如今也该都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也该都有了自己的儿孙,在他们的生命行将走向终点的今天,在他们每个和儿孙尽享天伦的时分,我不知他们是否还会想起,那些飘荡在宁波慰安所里未曾散去的哭声。
慰安所的去与留
2001年,旗杆巷47号傅家老宅因天一广场建造拆迁。前一夜,王景行几乎彻夜难眠。
这是他退休后着手调查日军在宁波设立慰安所种种罪行的第四年。在中国,慰安所的去与留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说他对于研究宁波慰安妇有种执念,可老人觉得,自己是在为后人留住日军侵华罪行的见证。他见过日军屠杀同胞的残忍,也听到过慰安所里撕心裂肺日夜不绝的哀哭。
为了保住这一处慰安所,他找了有关部门无数次。却也只能在痛心疾首里,看着它轰然倒地。
拆迁前的天一广场
没有人说的清,在宁波究竟曾有过多少慰安所,但在胡国忠的保守估计中,最少也有几十处。光奉化,有据可考的就有7处。
宁波城区共有4处慰安所:除旗杆巷47号洋房,被辟为“慰安所”,成为“军官俱乐部”外,药行街护城巷的大型浴室里,曾有专辟为日本人提供按摩和性服务的场所,在江北岸的外滩,也有一处日军高级军官的慰安所,名曰“东亚旅社”。但这两处早年间均已拆除。
“这最后一处,就是现存的玛瑙路41号,要不是王景行,恐怕也要没了。”胡国忠告诉我,这房子原为庄姓商人所有,还未造好就被日军霸占,并被装饰成日本人喜欢的风格,取名“月の家”,在日语中有性服务所的含义。“这一处旧址也是王景行考证出来的,因为有了前一次旗杆巷47号的教训,他考证确认后,就开始不断给书记市长写信,一直写一直写,锲而不舍。最后市里批了一百多万对这一处进行保护,这才使得宁波城区唯一一处慰安所旧址得以保存。”
这处王景行费尽心力保存下来的玛瑙路41号,如今成了江北区各部门的办公地,门口无明显标识。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却鲜少有人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什么。
“娃子们,以后把咱家的门可得看住了,再不能让人家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
说这话的老人名叫曹黑毛,慰安妇受害人,含恨死于2018年7月。
我想,这也是宁波的“慰安妇们”,想说,却未曾说出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