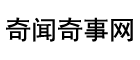应当如何理解王蒙小说《蝴蝶》中张思远的顿悟
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份危机及其疑似化解——重读[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王蒙小说《蝴蝶》的主题是张思远的身份危机及其化解,而这个危机本质上是知识分子革命者张思远的忠诚危机,它源于张思远的“革命者”身份突然遭到了他誓死效忠的革命组织的怀疑。这个危机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于: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张思远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这也决定了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的所谓“反思”根本不可能触及造成“文革”社会灾难(包括张思远自己的政治灾难)的根源。小说把反思的对象转向了所谓的干部“特权”和“作风”,即脱离人民群众,似乎重建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本文力图证明,这个重建身份认同的努力是经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和矫情的表演。
一、 革命文学中的忠诚主题
忠诚(以及与之相关的背叛)是常见于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以知识分子革命者/革命干部为主人公的革命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这是因为,忠诚话语只有在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内部才是有效的,它要求该组织成员必须保持对组织的绝对效忠。不同的政治组织之间不存在忠诚问题(即使它们通过协议方式组成一个更大的政治联盟,其间也只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忠诚关系,国共合作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革命文学中的忠诚问题常常成为纠缠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问题,而与反面人物(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等等)无关(革命可以对李玉和、杨子荣等提出忠诚要求,却不会对座山雕、胡传魁等提出忠诚要求)。与此同时,革命文学作品中有一类人物对忠诚问题又特别敏感,这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或革命者。[1]一方面,作为革命者或共产党员,他们是革命内部的“自己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缺少工农革命者的纯洁“血统”(阶级出身)。知识分子的身份是非常微妙的:既可以是革命的对象,又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既是“内部人”又是不可靠的“内部人”,既是“自己人”又是容易变节的“自己人”。这样,他们很自然地成为革命者内部对忠诚问题特别敏感的部分,是“组织”最不放心的部分,他们必须不断地向组织宣誓,不断表明自己的绝对忠诚。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坛,忠诚主题在以知识分子革命者/干部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得到了反复书写。因为这两个时期都有大量知识分子革命者/干部蒙受了冤屈,产生了大量冤案。所谓冤案,说穿了就是革命者的忠诚受到了组织不应有的怀疑乃至践踏。这些作品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所谓复出“右派”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他们的身份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或知识分子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书写自己的冤屈——比如是纠缠于自己的不幸遭遇还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原谅组织还是告别组织——就成为考验他们是否能继续保持忠诚的试金石,当然也是检验他们能否经由对自己冤屈的反思,达到新认同的建构和新主体性的建构的检测剂。
王蒙的《布礼》(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在这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2]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符合我们上面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所有规定:知识分子兼高级干部(《布礼》中的钟亦成是解放前的地下党,15岁入党的“少共”,《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是党的老干部,官至市委书记、副部长),也都在反“右”或“文革”中被打成“黑帮”、“三反分子”,“文革”后获得平反,重新成为革命干部(毋庸讳言,这两个主人公身上显然有作者的影子)。这样,主人公的忠诚危机及其化解方式,就成为解读作品的关键和枢纽(限于篇幅,本文只解读《蝴蝶》,《布礼》将另文解读)。
二、忠诚危机为什么如此可怕?
本篇小说名为“蝴蝶”,取典《庄子》“庄生梦蝶”以隐喻主人公的身份危机,有明显象征意义(这一点也与《布礼》中主人公“钟亦成”的名字相似)。[3]贯穿于整个小说的,正是张思远反复苦思的身份困惑:“我”到底是谁?张副部长还是“老张头”?“我”是一只变化不定的“蝴蝶”吗?“我”的归宿到底是哪里?首都北京(回到官员身份),还是山乡(彻底化身为农民)?与这个身份困惑相应,整部小说在语言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使用问句:设问、反问、自问自答、问了答答了再问,如此等等。
与钟亦成类似,张思远的认同危机源于他的“革命者”身份被突然剥夺,源于他与组织的血肉联系被突然割断,他一生誓死效忠的组织突然怀疑起他的忠诚了来了。[4]因此,张思远的身份危机本质上就是一个革命者的忠诚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可怕,根本原因在于:除了认同革命、忠诚组织,张思远根本不可能有别的任何认同或忠诚。在张思远的自我认知中,他完全是属于革命和组织的,他甚至就是革命、就是组织,而革命和组织也就是他。否定革命、脱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中篇小说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09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没有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喜怒哀乐。他几乎整整十七年没有休过假……离开了领导工作,就不存在什么张思远。”(第620-621页)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革命组织突然翻脸说:你张思远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革命的叛徒,是“反革命”黑帮。由于张思远和革命、和组织的二而一的关系,成为“反革命”的结果就是张思远彻底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人还是“臭狗屎”:“然而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张思远,一个弯腰缩脖、低头认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张思远,一个任别人辱骂、殴打、诬陷、折磨,却不能还手、不能畅快地呼吸的张思远。”这个张思远是“一个罪犯、贱民”,“一个被党所抛弃,一个被人民所抛弃,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丧家之犬张思远。”(第621页)于是,张思远产生了深深的迷惑:“这是我吗?我是张思远吗?张思远是黑帮和‘三反’分子吗?”(第621页)
对张思远这样的革命者,不但他的身份认同、思想意识是属于革命的,而且他的身体器官也是如此。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失去了革命者的身份,不但他的思想意识、而且他的身体器官全都彻底陷于混乱,陷于认同危机:
这个弯着的腰,是张书记——就是我的腰吗?
这个移动困难、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第621页)
可见,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张思远的控制和渗透是何等完全和彻底,渗透到了他的精神和身体器官的每一个细胞。
组织的逻辑、组织的力量就这样不可思议和神秘莫测,它可以转瞬之间把同样一个张思远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是不可一世的地委书记,一个是猪狗不如的反革命。两者之间的转化也是那样不可思议,一会儿威风凛凛,一会儿猪狗不如:“一夜之间,一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便变成了人人所不齿的狗屎,扬起的眉毛塌下来,刺人的目光变得可怜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焕发的荣光变得毫无血色。人们对这种挨斗的脸色有一种粗野的比喻,叫做被屁熏过一样”。(第619页)
这或许就是当时环境下张思远和所有其他个人的悲剧:无论干部还是群众,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够在组织之外、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之外获得自己稳定的身份认同乃至身体感觉。他们对于革命和组织的忠诚是无可选择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平等契约基础上的相互承诺和相互忠诚。这种效忠是单方面的、强制的:张思远必须获得革命和组织的认可才是人,否则就是畜生不如;而革命即使没有张思远也依然是一项摧枯拉朽的伟业,组织即使没有张思远也依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张思远没有自己定义自己、自己建构身份、自己选择忠诚对象的权利和能力(甚至都没有这种念头)。因此,即使忠诚被剥夺和否定,他也只能寄希望于革命和组织的回心转意,以便摆脱噩梦一般的变形记:
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个活着不如死了好的癞皮狗一样的“三反分子”、黑帮张思远不是他自身,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躯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标语上说:张思远在革命小将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不,这不是原形,是变形。他要坚强,要经得住变形的考验。(第621页)
但尽管张思远死不承认自己是“敌人”,苦苦坚持自己的忠诚,但他却不可能自己判断自己是谁,自己坚持自己的身份,因为极“左”意识形态和革命组织已经剥夺了他自己定义自己的能力,只有组织承认你是人你才是人。更有进者,组织可以宣告张思远“不忠”,但张思远却既不能拒绝这个宣判,说自己是被冤枉的(那就意味着组织错了);也不能接受——这是更加荒唐的——这个判断,从而真的变得不忠(那就变成了真正的叛徒)。他所能作的,只能是老老实实等待组织终有一天承认自己冤枉了一位忠诚的战士并为他平反昭雪。
显然,张思远没有也不可能理解自己的“变形记”“蝴蝶梦”是特定制度和意识形态环境下的身份悲剧。小说写到被打成“黑帮”、“三反分子”后,对自己命运“百思不得其解”的张思远最终把这一切说成是不可解释的“一场噩梦”,“一个误会”,“一个差错”,“一个恶狠狠的玩笑”,或不可理喻的“魔法”“法术”“变形”:“一个莫名其妙的驱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比喻把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灾难神秘化了,仿佛张思远们的命运是不可解释的宿命(这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对理性反思的回避)。在另外一些场合,张思远又把自己的命运视作“报应”:因为自己曾经积极参与了各种“整人”运动,打倒了从报纸副刊主任到市委宣传部长的一大批干部,“黑帮、牛鬼蛇神越抛越多,越抛越把自己裸露到最前线,终于,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该轮到他自己了。”(第620页)一个“轮”字就把张思远的悲剧原因遮蔽过去了,连一个具体的加害者都没有。[5]这种类似宗教轮回和报应的思想,根本不可能解释清楚张思远所处的特定环境中社会历史灾难的真正本质、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6]
三、劳动-人民拯救的神话
与《布礼》中钟亦成稍有不同,张思远并不是反“右”和“文革”政治运动的单纯受害者。小说写到他曾积极参与了从反“右”到“文革”初期的各种政治运动,参与了整人。在第一个妻子海云被打成“右”派后,张思远怒斥海云并与之离婚。这一切表明他在成为受害者之前并非清白无辜,他“文革”后自我反思和忏悔的根源也在这里(而《布礼》中的钟亦成基本上没有忏悔)。但非常奇怪的是:获得平反之后张思远应该反思的本来是极“左”时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才是造成反“右”扩大化、“文革”社会灾难以及张思远个人灾难的根源,也是导致张思远参与整人、给他人造成不幸的根源。但事实上他的所谓“反思”和“忏悔”根本没有涉及这些深层次问题,没有触及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的本质。[7]小说把反思的对象转换成了所谓的干部“特权”和“作风”(脱离人民群众),似乎组织和张思远本人以前的错误都在于脱离了劳动,疏远了人民群众,因此,重建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就能使一切迎刃而解。小说中张思远身份危机的克服就是建立在“劳动”和“人民”这两个宏大能指上的,重建与劳动以及人民的联系使张思远获得了新生。[8]
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张思远刚刚重访完自己落难时期劳动过的乡村,此刻正坐在象征特权的高级轿车上,带着“人民”的嘱托回京城上任(他已经升任副部长)。在后面的几乎每一章,都有大量篇幅写他对特权的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享受着特权,同时又在反思特权)。他心里装着秋文(“秋文”这个人物非常概念化和抽象化,这是一个代表所谓“人民”的符号,因此虽然比张思远年纪小,但张却觉得她像“自己的母亲”)的嘱托走上新的仕途:“好好地去做官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第605页)由此张思远重新得到了“人民”的授权,重建了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而且经过秋文(“人民”的代表)的点拨之后,张思远的另一个纠结和矛盾——回到城市还是留在农村,享受特权还是拒绝特权——也成功地化解了,因为宽容的、善解人意的“人民”说话了:“你们这些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淘换不来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头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摇头顿足骂你们。”(第645页)于是,官复原职、享受特权、与农民之间天差地别的各种差距就都变得合情合理了(“人民”自己都说了农民“只会摸锄头把子”),就成了“治国治党,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第645页)于是,心里装着“老张头”——另一个张思远,另一个“我”,已经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张思远——张副部长也就心安理得地回去做官去了(“如果张副部长和老张头谈谈,他并不感到不安”)。两个张思远(一个是副部长,一个是老张头)之间的分裂似乎也弥合了,不再存在了。
然而,这个通过劳动和人民来重建自己身份认同的努力是经不起分析的,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诡辩。
先来看劳动。1970年张思远被下放到山村劳动改造,并通过劳动重新了解自己。但张思远了解的是自己的什么呢?是自己的身体器官: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张纪的背和腰。在劳动间歇,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第631页)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描写,它告诉我们,劳动使张思远重新获得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比如新的政治信念),而是自己的身体。这倒是无意之中道出了实情:身体化的劳动的确只能使张思远获得器官感觉,而无助于克服由政治造成的张思远的忠诚危机和身份混乱,因为私人化的身体本来就是非政治的。通过劳动去反思反“右”和“文革”悲剧以及张思远自己悲剧命运的本质,无异于缘木求鱼,何其难也!
再来看看人民。在发现劳动和身体的同时,张思远还发现了人民(这和他的反思特权一致)。[9]人民对他的尊重和爱戴被美化为拯救力量:“十七年当中,他到处受到尊敬。但这尊敬一夜之间变成了诬陷、强暴、摧残。连美兰和他的儿子也离开了他。他恍然大悟,这尊敬不是对张思远二十市委书记的。他失去了市委书记便失去了这一切。但是现在不同了,农民们同情他,信任他,有什么事都来找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第631页)人民是纯洁的,朴素的,非功利的。但是作品中的这个所谓“人民”(“农民们”)是非常抽象的、无名的。就算这些“人民”真的淳朴善良,他们也不可能解决张思远因为极“左”政治的迫害而产生的身份危机、精神危机和政治信念危机。
何况,《蝴蝶》中的“人民”形象还是分裂的。如果作品中被赋予了拯救力量的“人民”是抽象空洞的,那么,不那么抽象的倒是作品张思远在升任副部长后故意放弃特权、坐普通硬卧时遇到的那些人(见小说中的“上路”章):那个态度粗暴的、势利眼的列车服务员,那个开口就骂“X你妈”的小男孩,那个邀请他打扑克的、“嘴里发出葱味”的胖子,以及那个排队买饭时蛮横不讲理地插队甚至要打他的汉子。这些更加具体的、粗鄙的“人民”,讽刺性地解构了秋文等代表的面目模糊的、被神化的“人民”(当然,无论是对火车上刁民的描写,还是对山村良民的描写,对于张思远由于忠诚危机而导致的身份危机及其克服而言,都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
从这些地方看,张思远副部长对于“人民”分明又是有些不屑的。就是那个似乎是张思远的另一半、代表“人民”的“老张头”,也是一个从来不会说话的影子而已,只有叙述人——也就是副部长张思远——才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副部长张思远在膜拜“老张头”的同时,也会流露出对后者的不屑:“老张头虽然轻松又自由,率直又天真,然而却又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无所事事。”(第650页)是啊,身负天下苍生重任的张副部长又怎么可以和这些平庸之辈同日而语呢?
故地重游部分是小说的重头戏,它承担着张思远“文革”灾难之后重获新生、重建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任务。这是一次重建身份的活动。考虑到张思远的认同危机是“文革”极“左”政治带来的(包括他自己所犯的追随极“左”政治的错误),他的身份认同的重建必须深刻触及到对这个制度和文化的重新认识,但是实际上这一切在小说中全部没有发生。张副部长放下繁忙的国家大事故地重游,为的是重建自己的政治信念,克服自己的身份为危机。但到下乡后他所见到的一切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吗?没有,无非是鸡鸭鱼肉、儿童时候熟悉的打枣场景、和乡亲们的原始情感之类。“枣雨”这部分写张思远故地重游时候的具体见闻和感受,全部是琐碎的日常生活叙事:“多么好啊多么好,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山村。一样的乡音,一样的乡情,一样的人心!一样的推推哪家的门都可以进,拿起哪家的筷子都可以吃,倒在哪家的炕头都可以睡!甚至连那几条老狗都没有忘记他,摇着尾巴向他跑来,伸起前爪扑他的腿,从湿漉漉的狗鼻子里发出撒娇的声音。”(第656页)不能说作者的描写不真实,问题是:这样的原始“乡音”“乡情”能够使得张思远克服政治认同、政治信仰的危机吗?不能,因为张思远的认同危机根本就不是源于远离了此类“乡情”、“乡音”。
所以,这次回乡之后的张思远和之前的张思远不会有什么本质差别。他的故地重游本质上是自己给自己做秀: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做给自己看:为自己重新享受特权地位寻找一个正当的理由。
四、让人纠结的特权
《蝴蝶》中的张思远翻来覆去在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自己享受特权是否应该。这种思考明显带有两面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好像一直在反思和讥讽自己的特权(与此相关的是讥讽自己的副部长或市委书记身份),作品一定程度上甚至带有这样的暗示:张思远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到农村劳动改造是罪有应得,因为他脱离了劳动,脱离了人民群众;但另一方面,张思远又要不断地为自己的复出(离开人民群众)辩护,也就是为自己继续享受特权辩护。
这样的折中立场决定了作品中既有大量对于张思远复职后的物质享受和特权的嘲讽,但这样的嘲讽又不能过于尖锐,必须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便为自己的复出后继续享受留下余地)。小说中有大段对部长楼的矛盾心理的描写(既留恋又有些鄙视)。值得注意的是,张思远在决定暂时放弃自己的特权时总是不失时机地着意提醒读者:他这是属于故意放弃特权,也就是说,他心里明白自己是特殊人物,是可以也应该有特权的:“他终于离开了部长楼,而且他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挂电话通知当地的各级领导准备接待。”(第646页)一个稳定地拥有特权的大人物故意放弃特权做一回“平民”(当然是暂时的),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获得道德上和心理上的优势,为了精神自救——给自己一个交代。正是由于这种特权的悬置是暂时的,伪装成“平民”的张部长才因此而获得了意外的观察力和审美乐趣:闷罐车里的张思远审视着甚至非常享受地观察着下层人物及其表情变化。
但对于官职和权力的留恋毕竟是第一位的和压倒性的,这点在他刚刚官复原职、回到市委小楼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白——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权力还刚刚回来,因此也就不能装得对它不在乎:“他又回到了市委小楼……镶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灯在最初的一霎那竟使他热泪盈眶了。幸好,谁也没有看见。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一句实在不应该想起的话。”(第639页)真是妙极了:只有百万富翁才有资本嘲笑金钱,同样,只有坐稳了权力宝座的人才有资本调侃这个宝座,这种调侃正是他的自信的表现。可见,张思远对劳动和乡村的赞美,对权力、地位和特权的时不时冒出来的妙趣横生又无关大局的讥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在继续享受现实中的特权的同时,又能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你看我虽然享受着特权,但是却并不迷恋它、甚至还有点看不起它。只有享受着特权的人才能获得讥讽特权的能力,只有官复原职之后的张思远,才能暂时悬置自己的身份,假装成为平民故地重游。故意坐破闷罐车回乡(仅此一次)既满足张思远的平民主义冲动,又可以让他在获得“人民”授权之后心安理得地坐着轿车和飞机(隐喻特权)回北京。这不是一种表演又是什么?
最后必须指出,张思远这一暂时悬置特权、以便更加理所当然地重新拥有特权的表演,果然为他赢得了道德的优势、人民的授权、内心的安宁,心安理得地回到了特权位置:再也不为自己的特权焦虑,相反坐在飞机上“安静地睡着了。”张思远不再犹豫不决、焦虑不安了,因为他虽然身回到了北京,但“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装到自己心里,装到汽车上带走了。他一无所得?他满载而归。他丢了魂?他找到了魂”。(第664页)
这大概就是一种张思远式的知识分子兼高官的聪明智慧:反思特权又不拒绝特权。作为高官,他当然要享受特权(因为他是“为人民服务”),作为知识分子,他当然要蔑视特权(哪怕是装样子)。[10]
回到北京那个部长楼后的张思远舒服地洗着澡,再次享受特权和高级生活,但已经没有任何不舒服和内疚,而是很舒服、很心安理得了。这个时候,特权生活的符号意义已经完全发生了倒转,它不再是使张思远坐立不安的脱离人民的标志了,因为他下过乡了。
王蒙 的《蝴蝶》的原文是什么?
王蒙 《蝴蝶》原文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像1956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儿,不也是这样自得地呜呜叫吗?汽车开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眼前闪过村庄、房屋、自动列成一队向他们鼓掌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车投掷石块的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地看着他们的农民,比院墙高耸起许多的草堆,还有树木、田野、池塘、道路、丘陵地和洼地,堆满了用泥巴齐齐整整地封起了顶子的麦草的场院,以及牲畜、胶轮马车、手扶拖拉机和它所牵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时候被山洪冲坏了的裸露的、受了伤的砂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尘土和由于驭手偷懒、没有挂好粪兜而漏落下的马粪蛋,全都照直向着他和他的北京牌扑来,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从他身下蹿到了他和车的身后。指示盘上说明越野小车的时速已经超过了60公里。车轮的滚动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车轮轧在地面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敏捷的、轻飘飘的沙沙声,这种沙沙声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在冰场上滑冰,在太液池上划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坚持长跑,穿一身海蓝色的腈纶秋衣秋裤。该死的汽车,为什么要把他和地面,和那么富有,那么公平,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污染的新鲜空气隔离开来呢?然而坐在汽车上是舒服的。汽车可以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在北京,人们认为坐在后排才是尊贵的,驾驶员身旁的那个单人的座位则是留给秘书、警卫人员或者翻译坐的,他们时时需要推开车门,跳下去和对方的一位秘书、对方的警卫人员或者对方的翻译联系,而作为首长的他,则呆呆地坐在车后不动。甚至当一切都联系好了的时候,当他的秘书或者别的什么人打开后车门探进头来,俯着身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也是懒洋洋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时他接连打两个哈欠。许多时候他要等秘书说了两遍或者三遍以后才微微地点点头或摇摇头,“嗯”一声或者“哼”一声。这样才更像首长。倒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他实在太忙。只有行车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片刻的解脱,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时也还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小事情他都无须过问,无须操心,无须动手甚至无须动口。那是什么?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安排坐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安稳。离开山村的时候,秋文和乡亲们围着汽车送他。“老张头,下回还来!”拴福大哥捋着胡须,笑眯眯地说。大嫂呢,抹着眼泪,用手遮在眼眉上,那样深情地看着他。其实,并没有刺目的阳光,她只是用那手势表示着她的目光的专注。秋文的饱经沧桑,仿佛洞察一切的悲天悯人的神情上出现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期待和远眺的表情,他们的分别是沉重的。他们的分别是轻松的。这样,如秋文说的,他们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在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多想的吗?秋文说:“好好地做官去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着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她缓缓地、微笑着说,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悲凉,她说得那样平稳,那样从容,那样温存又那样有力量。一刹那间,她好像成了张思远的大姐姐,她好像在安慰一个没有放起自己制作的风筝因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实,她比老张要小好几岁呢!其实,老张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快60的人了,在他那个圈子里却还算作“年轻有为”。古老的中国,悠久的中华!这些年,青年人的年龄上限正像转氨酶实验阳性反应的上限一样,大大地放宽了。过去,转氨酶120就可以确诊肝炎,现在呢,转氨酶200还不给开病假条呢!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冬也丢在了那边。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粪叉,把背篓和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榆叶山芋小米饭……全都丢下了。秋文和冬冬,这是照耀他这个年轻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是照耀他的无限好的夕阳,他把夕阳留在了长满核桃树的云霞山那边。夕阳对他招着手,远去了。一步一远啊。这是文姬归汉时所唱的歌词。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车,车轮的旋转使变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他的身边呢?为了冬冬的母亲——海云,那棵颤抖的、被碾碎了的小白花,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的。然而他挂牵着冬冬,冬冬还只是一颗在地平线上闪烁,远远还没有升起来的小星星。这颗星星总会照耀他的。他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对于下一代的过分的关心,过分周到的安排,给下一代提供的过分优越的条件和为了防范下一代而划地为牢的一切努力不仅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着冬冬,这个连他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一的儿子。他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虽然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何况这一代青年成长在颠倒和错乱的年代,他们受了太多的骗,他们有太多的怀疑和愤怒。但是,冬冬是太过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历史,能够了解现实,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走上歧路。他希望儿子的可以原谅一部分的偏激不致于向害己害人害国的破坏性方面发展。1、【简介】:《蝴蝶》是王蒙的一篇充满反思力量的佳作。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是一个带着自审自责意识反思灵魂异化的独特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真诚的少见的反思主体。2、【作者简介】:王蒙是当代中国创作力最旺盛、影响力最大的作家,本书则是他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作品精选集。王蒙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创作主体并不穷尽于任何一部或一个阶段或一种文体的作品中,作家王蒙的整体形象犹如百变蝴蝶,是不断被创造出来的、丰富复杂、难以定型的存在。因此,本书的编辑方式最能反映王蒙五十年来的创作实绩。本书精心汇集王蒙各体文学创作凡九十九篇,八十余万宇,分小说、散文随笔、怀人小品、国外游记、学术杂俎、作家论、文学与文化综论以及诗歌,共八辑。编者根据自己的长期探索,同时吸取了学术界近三十年来王蒙研究的成果,在每一辑之前都撰写了认真负责的导读,因此本书不仅给读者提供了系统而精深地读解王蒙的机会,也具有相当的学术参考价值,值得爱好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广大读者收藏。
请问王蒙的《蝴蝶》到底是意识流的手法还是蒙太奇的手法?快
(1)《蝴蝶》具有哪些意识流小说的特征?
①部分地采用心理时间
②幻觉与实觉相混合,意识与潜意识相交织
③内心独白
④立体的放射性结构
(2)《蝴蝶》中,王蒙对意识流的东方化改造
①情节与情结相结合的双线复式结构
②“意识流”成份并不呈现为统一的不可分散的流
③虽有潜意识表现却并非以潜意识为中心,虽然写了性,却不是泛性主义
王蒙的作品被认为是“东方意识流”,主要是因为在情节发展中融入心理结构,从心理角度处理时空关系。然而王蒙并没有以人物的意识流动作为贯穿作品的主线。
王蒙小说的语言风格
王蒙的作品一直贯穿着理想主义的主题,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 改编电影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依然没有抛弃早年的理想主义精神,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对历史理想主义的认同,王蒙相信,不管实现理想的道路有多么曲折,但前途总是光明的。也正因为这样,王蒙在对他心中的理想主义精神讴歌的同时,也冷峻的指出了实现理想的艰难性与反复性。正如王蒙在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他一直渴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却不得不在文革的夹缝中小心翼翼的处理着各种问题,从省委高官到被打倒的反革命,再下放到农村改造,看上去张思远似乎离他的理想越来越远,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那样的努力却依然触碰不到他的理想,但是最后,文革结束,他不仅平了反,还升了职,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敬,张思远远在天边的理想又再次回到指尖。小说中的张思远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也影射了王蒙在实现理想主义精神的时候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