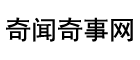我弥留之际的创作背景
福克纳是在1929年10月25日(星期五)开始写《我弥留之际》的,当时他正在密西西比大学发电厂里监督那些上夜班的工人。当时,福克纳正处于经济危机和艺术枯竭的时候,而美国的灾难(1929年的大萧条)使他的处境更为恶化。有关“繁荣的20年代”的故事开始从报纸中消失,接下来的“30年代”或“大萧条时期”已经开始。然而,他周围的许多人都不相信他能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因为他以前作品的销售情况很让人失望。在福克纳从老一辈作家比如约瑟夫·康拉德等那里借鉴了一些写作风格。另一个有影响力的作家是舍伍德·安德森,其小说《小镇畸人》中的故事为描写《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伦一家(the Bundrens)的环境提供了额外的灵感:福克纳赋予这个家庭以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同样,詹姆斯·乔伊斯在他史诗般的《尤利西斯》中的内心独白也被福克纳用在他的小说中。影响稍少的要数T·S·艾略特的那些描写孤立之人的诗歌,尤其是《空心人》和《荒原》了。 从字面上说,《我弥留之际》讲的是小说中本德伦一家的女主人艾迪临死以及死后发生在这一家人身上的故事;但从比喻意义上说,《我弥留之际》之中的“我”可以暗指刚刚过去的“繁荣的20年代”,它虽已成过去,但是其影响还深深地留在美国人们的脑海里,20年代还在“弥留”着。毋庸置疑,福克纳在小说中触及到了存在于当时美国社会中的许多社会现实问题。鉴于该小说的重要性以及它创作和发表的时间来说,可以说,《我弥留之际》是20年代创作的最后一本重要的美国小说,也是在30年代发表的第一本重要的美国小说。 在20年代,美国南方地区仍然在努力从1860年代的内战以及战后北方对南方的经济殖民中恢复过来。南方的农民已经处于长期的萧条时期了。在30年代,各种各样的合作行为几乎在整个美国都得到了鼓励。全国范围内,“集体主义”成了一种口号。在南方,平民党党员(Populist)和各种激进运动人士都在为提高弱势群体,尤其是贫穷白人农民们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而斗争,即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去反对富有的种植园主和银行联盟者。虽然当时平民党主义(populism)的影响在不断扩大,但对南方而言,“集体主义”的故事却有着特别保守的涵义。从传统意义上说,南方的集体主义理想意味着一种对长期存在的集体关系和风俗的尊重。它意味着要讲究礼节形式。福克纳把南方这种集体主义理想写进了小说中。 1930年1月12日,福克纳打完了《我弥留之际》,之后他便筹划投稿给一些有知名度的杂志,这些筹划中的小说有30篇于将来的3年中发表。这时他的短篇小说稿酬已超过过去写四部长篇的酬劳。4月30日,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发表于《论坛》杂志,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还有《荣誉》、《节俭》和《殉葬》。10月6日,《我弥留之际》在纽约由凯普与史密斯公司出版。12月,同一公司出版了修订版的《圣殿》。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在其演说中提到了福克纳,称他“把南方从多愁善感的女人的眼泪中解放了出来”。
《我弥留之际》发生了什么?
1929年,时年30岁的威廉·福克纳还是一个啃老族,时常靠老爹和亲友接济过活。为了糊口,在密西西比大学发电厂锅炉房找了一个差使。工作间隙,仅用六个星期就完成了其长篇小说双壁之一的《我弥留之际》。没有人想到,包括他自己,20年之后,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这个矮个子米国人会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力压加缪、斯坦贝克、海明威、帕斯捷尔纳克等一众文学大咖,成为文坛盟主。
我们一度离那些传奇人物的时代如此之近,可是仍然无法亲眼目睹本尊的风采。李小龙1973年的突然离世,让人痛心疾首。披头士的分崩离析和笛农的惨遭枪击,让人唏嘘叹息。而福克纳他老人家,历经艰苦卓绝的笔耕生涯、多年的酒精浸泡、不和谐的婚姻,情人的离去,世事的煎熬,也已于1962年过世。
他们逝于似可触摸的现代,我们努力尝试伸手去抓住他们,探求那些一直存于心底的悬念,然而终不可得。所以还是回到他们留下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回到那些跳跃的音符,忧伤且悲天悯人的文字中去吧,去感受那不一样的灵魂,获得别样的人生和心理体验,倾听穿越时空的声音。
两个多月来,在写了六万余言。刚提笔时,我也曾想写些碎碎念,小确幸,鸡汤文,可是我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的生活体验不够丰富多彩,治学的领域不够广阔,思想还不够深邃。再说了,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听别人唠叨、说教,因此就着力写了一些电影故事和生活中的趣事,希望有缘的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趣味,假如能再受到一点启发,那就感恩不尽,倍感欣慰了。
围绕《我弥留之际》,各路贤达已然从所谓的叙事结构、思想性、艺术性上作了深入剖析,此处不再赘述。本文仍然重点从故事本身角度,看《我弥留之际》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些什么样的启示。
安迪出生在杰弗逊镇,嫁到约克纳帕塔法郡,那里也是福克纳的家乡。从小到大,无数次听到她那悲观厌世、秉持虚无主义人生观的父亲嘟囔一句话:“人生就是一个慢慢躺向棺材的过程,一切都是为了那最终的安息和永恒做准备。”
这论调在安迪耳畔重复N遍后就成为了她一生都在探究证明的命题,然而内心深处却依然对彼岸心存向往。这种生活态度造成她人格的分裂,一面消极地忍受着生活的艰难困苦和不如意,一面自怨自艾,试图逃离现实,奔向爱情和幸福的彼岸,求得心灵的宁静。
在娘家时不安于乡村女教师的乏味生活,总是一个人到山后的泉水边静思冥想,在泉水的叮咚声中独处,才能片刻找到自我,甚至通过体罚学生宣泄自己的压抑,求得个人的存在感。
农民安斯·本德伦看上她,驾着马车,一次次佯装不经意经过她的学校,用笨拙的方式接近她。渴望改变生活状态的安迪,顺势上了安斯的车,成为了他的妻子。
走进婚姻,连生卡什和达尔两子,安迪发现自己离彼岸更加遥远,就连体味孤独都已变得奢侈,山后的那一泓泉水也不复存在。她深切感受到自己并不爱安斯,只是沦为了别人的婆姨,成为了哺乳的工具。面对困境,她顿悟到在娘家的时光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光阴。安迪早早地就向安斯提出要求,死后要叶落归根,葬在四十英里外的杰弗逊镇。既然是安斯把她从原来的生活中带走,那么要求他把以前的生活还给她,倒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二儿子达尔出生后,她再也不让安斯近身。禁不住对爱情的向往,她与牧师惠特菲尔德暗通款曲,生下私生子朱厄尔。然而牧师也只是个多情的牧师,涉及到自身的利益,惠特菲尔德适时退出了这感情的游戏。
在爱情里挣扎了一番,安迪除了私生子一无所获。安斯知道自己头上戴了一顶大号的绿帽子,不过安斯不说透,牢牢吃定了安迪。
除了在这清苦之家苦熬,安迪没有别的出路,安斯的沉默又让安迪充满负罪感,于是安迪用肉体作为出轨的补偿,又为安斯生了一儿一女,瓦达曼和杜威。
刚过中年的安迪,失去了与无聊和疲累时光对抗的耐心,不再对彼岸充满向往,重病缠身,躺在床上不吃不饮,只有眼睛还能动一动、听一听、说一说,气若游丝,已然是弥留之际。
大儿子卡什是个优秀的木匠,母亲甫一进入弥留光景,就开始为安迪打造棺材,整个院子里没完没了地响着锯木锛槽的声音,仿佛死神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二儿子达尔和私生子朱厄尔却在母亲即将辞世之际,为了挣三块美元,急急慌慌带着牲口去跑运输,错过了与母亲的最后一面。
女儿杜威时刻在病床前守护着母亲,一边用扇子给母亲降温,驱除先知先觉的苍蝇,一边却在纠结如何打掉与乡邻莱夫偷情怀的孩子。
小儿子瓦达曼尚未成年,目睹母亲的逐渐离去,只能在打鱼捉鸟中排遣悲伤和恐慌的情绪,在他的感觉中,妈妈就像他偶然捕获的那条巨大的鱼,正卑微地死去。
回光返照的一天终于到来,安迪挣扎着坐起来,凝望窗外为自己打造棺木的长子,卡什曾无数次在做木工活时,回头与窗户里的母亲对望,他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注视活着的母亲,他远远地向妈妈比划着棺材的形状。
安迪将目光划过女儿,最终停留在幼子身上,重新躺下,生命迅速离开了躯体,她至死都没有看一眼身边的丈夫。
安斯注视着死去的妻子,嘴里却不由自主地说:“上帝的意旨就要实现了,可以去装假牙了。”
入殓的那个晚上,下着大雨,卡什在雨中完成了棺木最后的一道工序,乡邻与家人一起将安迪抬进了最后的存身之所,她的身体像空气一样轻,灵魂仿佛带走了一切,不知她最终是否找到了彼岸。
暴雨如注,河水眼看着向堤岸逼近。女人们围着棺木唱着圣歌。牧师惠特菲尔德冒雨赶来主持入殓仪式。他想向安斯忏悔,可是想到安迪已经离世,又失去了忏悔的勇气,还是将这往事埋在心底。男人们无聊地听雨,讨论着某处的木桥已被洪水冲走,担忧着何时才能启程前往杰弗逊。
最小的儿子瓦达曼趁人不备,用卡什的钻头将棺木钻了几个眼,似乎想把安迪再弄出来,用力之大,甚至在安迪脸上钻出了洞。
三天后,达尔和朱厄尔赶回家,一家人终于踏上归葬安迪之路。
卡什坚持要带上工具箱,因为路上要顺便给邻人塔什修缮屋顶。大车出发不久,安迪尸骨未寒,达尔就在棺材边谈笑风生,放声大笑。杜威攥紧莱夫给她的10块钱,准备到镇上找个大夫把孩子拿掉。瓦达曼则一心想着买下镇上玩具店里的小火车。而一家之主安斯,则想着假牙的事。安迪在棺材里静静地躺着,她的身体随着路面的颠簸起伏。
朱厄尔拒绝和一家人一起坐大车,坚持独自一人骑马前往,这做派倒也和他私生子的尴尬身份契合。那匹枣红马是他彻夜不停劳作,为乡邻耕了四十亩地的所得,是他的精神寄托。
安斯不愿欠别人的情,谢绝了沿途乡亲们入户休憩就餐的邀请,一家人晚上就睡在大车周围,吃带来的干粮。
终于来到河边。连日大雨,已将木桥基本淹没。安斯拒不听劝,坚决不绕道,带着女儿、幼子和弗龙(一个过来帮忙的乡邻)冒险过桥,却安排三个儿子驱车涉水过河。
朱厄尔骑马在前面带路,达尔和卡什在后面赶车。水流湍急,上游不时冲下圆木,左躲右闪,还是被圆木撞上,车翻骡死。
不会游泳的卡什攀住朱厄尔枣红马的马鞍,在水里憋着气,最终浮出水面才免于一死。好在卡什和达尔拼命保住了棺材,没让安迪顺流漂走成为浮尸。
卡什视若生命的工具箱落在河里,朱厄尔反复潜水,带着大家将工具逐一打捞上来。
卡什虚弱的一句话说不上来,不断从口里往外冒水。这时家人才发现,卡什一条腿已经在涉水中被马踢断。
一身干爽的安斯不住地叹息:“天底下还有比我更倒霉的人吗?!”然后就自作主张,用家里的农具、卡什兜里仅有的八美元积蓄,朱厄尔拼命赚来的枣红马换了两匹骡子。
闻听安斯拿自己的马去换骡子,朱厄尔大爆粗口,骑着马箭一样跑了,大家都觉得这笔买卖是泡汤了,杰弗逊看来是如此遥不可及。
然而那两匹骡子终于还是套在了大车上。朱厄尔亲自将马骑到了买主的家里。
归葬之路再次启程。尸臭无处不在,十几只秃鹰围着棺材飞旋,瓦达曼将他所有的精力都用来驱赶秃鹰。
卡什断腿的夹板总也固定不住,安斯不舍得再去看医生,安排孩子们买了水泥,掺上沙子,敷在断腿处,然后再绑上夹板固定。卡什感觉断腿一阵阵的灼热,却对父亲和兄弟们说:“谢谢你们,我好多了,不要因为我浪费时间了。”
烈日烤灼,卡什觉得腿上热的受不了,剧烈的疼痛让他满头大汗,杜威帮他解开夹板,往水泥上浇水降温,最终还是叫了医生,敲碎水泥,断腿大面积灼伤,已然变成黑色。
达尔是五个孩子中最具洞察力的一个。他象一个先知,洞悉一切,对这一切愚蠢的事心怀不满。他知道杜威的小秘密,也知道朱厄尔来路不明。没有人乐意自己的秘密被人洞悉,因此全家人都与达尔存着戒备之心。在艾迪弥留之际,他和朱厄尔在外面挣那三个美元的时候,他似乎感到什么,突然对朱厄尔说:“艾迪已经去见主了。”
达尔本不赞成按死去人的意愿行事。然而啥事都逃避应付的安斯,这次却认真起来,一定要履行对亡妻的承诺,见人就絮叨自己历尽万难实现对亡妻承诺的不易。本可就地安葬的平常事,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非要倾尽全家之力踏上这苦难的历程!
冲天的尸臭,卡什的断腿、朱厄尔失去的马,淹死的骡子,耗尽的心神,达尔觉得这苦难如此不堪不明,看着家人在归葬的幌子下各怀鬼胎,他觉得厌恶。
苦难的送葬路走到了第九天,即将大功告成之际,达尔一气之下将存放棺材的草房点燃,而这一切都被时刻关注秃鹰动向的瓦达曼看进眼里。
朱厄尔奋不顾身从火光中抢出了安迪的棺木,严重的烧伤让朱厄尔与娘亲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历经十日,臭气熏天的大车终于赶到杰弗逊城。整个城市弥漫着安迪的味道。
杜威带着瓦达曼,去药房和商店。药店的伙计冒充大夫,给杜威假药,还以检查为名,带到地下室诱奸了她。杜威魂不守舍,拿着那些食品做成的胶囊喃喃自语:“我知道那不管用,我知道那不管用……”
瓦达曼望车兴叹,那橱窗里的小火车寄托着他的梦想,可是却似乎永远与他无缘。
瓦达曼告诉杜威:“那火是达尔放的”,担心怀孕的事被达尔泄露,杜威悄悄告发了达尔。
两个带枪的警察带走了达尔,杜威扑向达尔又抓又挠。朱厄尔则恨恨地对着达尔喊:“杀死他,杀死那个狗娘养的!”
安斯夺走了杜威的10块美元,配上了假牙。他们没有带上挖墓穴的铁锹,安斯去不认识的人家借了两把,这一趟还认识了一个长得像鸭子的女人。
安迪终于入土为安,配上假牙的安斯意气风发,带着那个像鸭子一样的女人走向他的儿女:“见过本德伦太太吧。”
1.关于意识流
故事如此简单,可福克纳硬是把它写成了长篇。那条吞噬了两头骡子,卡什慌乱间断腿的河流,对,就是它,它就是这篇小说最形象的感觉,意识的河流!
30余个人物,59个独白章节,每个人面对死亡这个大事件的精神世界,都纤毫毕露地描摹出来。众人的心理和意识,汇成了滔滔大河,裹挟着一切,推动着事情向着荒诞不经,却又命中注定的结局流去。
存在决定了意识,还是意识决定了存在?我已被这滚滚河流冲得意识不清,人事不醒。
《我弥留之际》在文本上有些晦涩,在阅读体验上有时会很突兀,经常会有不明就里、找不着北的感觉,导致有时由于急于想知道后续的故事情节,会采取跨越式的阅读方式,人为地忽略了一些精彩的章节。上述种种,我想那是因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智力的人,对待时间、空间以及同一事物的看法、印象会有很大不同,才会在同一本书的意识流文字上出现落差,这种阅读体验有时会很刺激,会有一种进入他人脑洞的感觉。
所以《我弥留之际》这类书,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最好的阅读方式是看到、遇到这本书,就随意翻几页,长此以往,就能把各个人物的意识串联起来,逐渐加深对福克纳思想的认识。毕竟,书中所有人物的意识,都是福克纳制造出的意识。
平心而论,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等同类小说,心不静是无法读的。
2.关于小说文体的优劣
传统小说注重以情节、情景塑造一个现实世界,意识流小说注重以意识和意象构筑一个精神世界。
前者恰似隔着轻纱看人性,后者好像拿着手术刀,将人的身体剖开,仔细翻看心脏每一个脉络的走向。
客观说,二者无所谓优劣,文体是为主题和思想服务的。个人认为,二者有机结合是最佳文体。
《我弥留之际》在文体上偏重意识流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