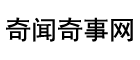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坚持采用秘密方式写作的"七月诗派"诗人是谁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坚持采用秘密方式写作的“七月诗派”诗人是绿原。绿原(1922— 2009),原名刘仁甫,曾用译名刘半九,湖北黄陂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诗坛广受关注,早期诗作《小时候》被收入台湾教科书。抗战胜利前后,绿原的爱国战斗诗篇,在进步学生和年轻的读者中广为流传,为“七月诗派”后期重要代表之一。1949年后曾在长江日报社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 因受胡风案件牵连,丧失自由七年,在囚禁中自学掌握了德语,获释后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980年胡风案件平反,恢复中共党籍,离休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扩展资料绿原的主要作品:绿原一生历经磨难,解放前曾遭遇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在大学即被通缉而不得不离校逃亡,但他始终珍惜与诗神相遇合的缘分,生平著作等身,著有《童话》、《集合》、《又是一个起点》、《人之诗》、《人之诗续篇》、《另一支歌》、《我们走向海》、《绿原自选诗》、《向时间走去》等诗集。《绕指集》、《非花非雾集》、《苜蓿与葡萄》、《再谈幽默》、《寻芳草集》、《半九别集》、《绿原说诗》、《寻觅集》 、《沧桑片羽》 等文集。
绿原《又一名哥伦布》原文
我们的诗人将自己想象成为二十世纪的哥伦布。
如同五百年前的那个哥伦布一样,
他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
不同的是,哥伦布是自愿,而他是被迫这样做的﹔
不同的是,哥伦布有着众多的水手,而他是独自一人。
他的“圣玛丽娅”不是一只船,
而是,“四堵苍黄的粉墙”,
他不是航行在空间的海洋,
而是在“永恒的时间的海洋上”。
“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运动”,
他孤独地在时间的海洋的波涛上沉浮。
谁能想象他的无边的寂寞,他的深沉的悲哀?
然而,这个哥伦布像那个哥伦布一样,
任何风浪都没有熄灭他内心的火焰:
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
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
飘流在时间的海洋上
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
坚信前面就是“印度”
──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
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诗人绿原的简历
绿原简历 绿原,生于1922年,曾就学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4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童话》。因“胡风案件”丧失过25年写作权。被囚7 年自学德语,重返社会后从事德语文学编辑工作。出版诗集:《童话》、《又是一个起点》、《人之诗》、《另一支歌》、《我们走向海》、《绿原自选诗》等;译诗集:《请向内心走去》、《拆散的笔记簿》、《浮士德》、《里尔克诗选》等;文集:《寻芳草集》、《绿原说诗》、《半九别集》、《绿原文集》等;译文集:《德国的浪漫派》、《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等。诗歌创作获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 C奖项,译著《浮士德》获“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辑,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作家牛汉原名是什么?属于什么诗派?
原名:史承汉或史成汉
诗派:七月诗派
生平简介:
牛汉(1923年10月2日-2013年9月29日) ,本名原为“史承汉”,后改为“史成汉”,又名“牛汉”,曾用笔名“谷风”,山西省定襄县人,蒙古族。当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194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写诗,近20年来同时写散文。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他创作的《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半棵树》等诗广为传诵,曾出版《牛汉诗文集》等。
牛汉于2013年9月29日7时30分在北京家中病逝,享年89岁。他的追悼会在10月9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11月29日上午,人民出版社在京为其举行追思会。
名字由来:
牛汉,1923年10月生于山西定襄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原名史承汉,因为上了两年小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对,总把 “承”字写错,被父亲改为史成汉(在文章《我的第一本书》中提到过),曾用笔名谷风,远祖系蒙古族,原名叫“承汉”的原因不明。
七月诗派: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建国后,该诗派领导人胡风被批判,该诗派走向衰落。文革后,牛汉等编辑了诗集《白色花》,是著名的七月诗派重新引人注目,绿原、牛汉、曾卓等人在新时期的诗歌创作,特别是那些最感人的诗篇,大都记录了他们在建国后所经历的“苦难历程的心理内容。
代表诗人: 艾青 胡风 田间 彭燕郊 牛汉 鲁藜 绿原 阿垅 曾卓 杜谷 邹荻帆。
绿原的《萤》怎么赏析啊?
作者:张立群 提交日期:2007-4-26 14:53:26楼主 作为绿原的诗友,著名诗人牛汉曾经在《荆棘与血液——谈绿原的诗》一文中这样评价过:“从诗的角度来说,我倒觉得绿原诗里一直有着一种时起时伏、若明若暗的理念化倾向。”[1]而在《绿原的诗》一文中,著名诗歌评论家周良沛则又有“绿原诗中表现的全部知性,起先都是来自自身的不幸遭遇和各个时期在底层人民之间而有的活生生的感受、思索和剖析,以及同时接受的先进的——由切合抗战现实的民族的、爱国的思想到马列思想的引导。由于有这些思想准备,他又是诗人,必定会发而为诗,发而为‘知性’强的诗,但决不是概念化的诗的哲理和哲理的诗。有思想的自觉,有艺术的自觉,才有‘将太阳同向日葵溶解在一起’的诗。”[2]虽然,上述两种评价在表面的概念使用上存有不同,但如果联系诗人绿原的具体创作和生活历程的话,我们似乎不难发现:诸如“理念化”、“知性”以及“哲理”等词语(事实上,关于类似的论述远远超过以上所列举的)尽管有语义色彩和程度之间的差别,但它们在具体指涉绿原的诗歌时,其整体含义却是基本相同的,即这些词语最终所要说明的都是贯穿绿原诗歌写作中的“理性化色彩”。那么,这种“理性化色彩”究竟如何在绿原的诗歌写作中予以呈现并展开其历史情境的呢?所谓“熔铸的执着”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进行阐述的。
一
尽管,最初登上诗坛的绿原是以《童话》诗集的方式,让众多读者在他的“童音”与梦一般的天国中迷醉,而徜徉于其“童话”中那奇妙、梦幻与淡淡哀伤的境界,也会让令人不自觉的想起曾经一度流行于30年代诗坛的、如卞之琳式的现代派诗歌[3]。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诗人也往往在类似“不是没有诗呵,/是诗人的竖琴/被谁敲碎在桥边,/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 杀死那些专门虐待青色谷粒的蝗虫吧,/没有晚祷!/愈不流泪的,/愈不需要十字架;/血流得愈多,/颜色愈是深沉的。// 不是要写诗,要写一部革命史啊。”(《憎恨》,1941年)的诗句中,以“浑身都是敏感的触角”[4]的方式传达出诗人当时险恶的生存环境,以及战争的烽烟正焚毁那一个个如梦般的“童话”。而后,在建国前7年的时间里,绿原便进入了其怒张式的政治抒情诗时代。在《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1944年)、《终点,又是一个起点》(1945年)、《复仇的哲学》(1946年)、《伽利略在真理面前》(1946年)等作品中,绿原不但关注时代风云以及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物的命运,而更为重要的是,绿原正在这些具有时代性和战斗力的诗篇中和过去的自我进行“告别”。于是,在诸如“有战士诗人/他唱真理的胜利/他用歌射击/他的诗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诗人》,1949年)、“人活着/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云彩”(《航海》,1949年)的诗句中,诗人对真理的追求、战士的认可、人生的理解正以理性融合情感的方式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建国前在绿原诗歌中呈现出的“理性化色彩”以及诗风前后的转变,除了与诗人自觉反叛当时黑暗专制社会以及适应时代要求有关外,还与埋藏于绿原心中的幼年生存体验有关。绿原从小父母双亡,是在比他年长十九岁哥哥的抚育下长大成人的。父母的过早离世、几个姐姐相继送人当了童养媳,以及生活的清苦,不但使他缺少儿时的快乐,而且也造成了他身体上的羸弱以及性格上的内向、心灵上的孤寂。这种现实的生存环境不能不在诗人幼年的记忆中留下所谓“苦难的心理原型”,因而,虽然最初的绿原是以一种单纯、透明、充满幻想的“童音”方式登上了诗坛,但这种在详细考察诗人生平之后的“独特表达方式”除了是寄予一种对不幸童年的精神补偿外,更多是在于具体表达方式与创作风格上的不同。而一旦外在的环境再度发生变化和诗人自我逐渐在成熟的嬗变中走向广阔的“大我”空间后,那么,这种潜在的因子就会适时而发,并在犀利与备份中释放出哲理与思辨性的色彩。而从“童真”到“莽汉”的转变过程不但是绿原建国前诗歌创作的整体趋势,同时,也无疑是符合诸如“七月诗派”那种融合时代、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之“创化”的历史特点的。[5]
自1949年下半年创作出《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1959年写成《又一名哥伦布》之前,绿原进入了他创作上的一段“低回时期”[6]。在这一时期内,虽然新中国的诞生让诗人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但由于长期忙于机关工作,无法更深入地进入到生活的内部,所以,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诗歌大多显得有些空泛乏力,而这,对于始终在诗歌创作上有不懈探索精神的绿原来说,无疑是可以明显感受得到的。写于1953至1954年间的《雪》(1953年)、《快乐的火焰》(1954年)、《小河醒了》(1954年)等作品,是诗人努力摆脱束缚之后的创作,其朴实、活泼、自然、明朗的生活气息曾一度让人耳目一新。然而,无论就当时的发表机会,还是1955年的身陷囹圄,都使得这种探索被人为的中断了。
1955年5月13日,绿原因“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至此基本中断创作达20余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获得重新发表作品的机会。然而,监狱的生涯并没有使其意志彻底消沉,在1955至1962年单身监禁的七年里,绿原虽然在心灵上遭受炼狱式的煎熬,但他依旧通过顽强自学的方式,练就了德语翻译的技能。对苦难的反复咀嚼和深入灵魂的体验,不但使其意志得到了巨大的磨练,同时,也为其深刻认识人生、社会、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著名的“潜在写作”文本《又一个哥伦布》(1959年)、《手语诗》(1959年)、《面壁而立》(1960年),以及完成于十年浩劫中的《重读〈圣经〉》(1970年)、《信仰》(1971年)等均在“理性化色彩”方面达到了诗人的顶峰。与此同时,诗人也由于其坎坷的经历、中年的成熟心态,渐次达到了诗歌艺术与自我人格意义上的双重成熟。在最近一次接受访谈中,绿原在回忆80年代初期重获新生后的具体诗歌创作时曾经说道:“停笔二十多年,到八十年代重新拿起笔来,我发现距离自己过去的艺术思维很远了,对过去的作品几乎不认识,在感情上已经无法相互交流。原来我已开始变成一个老人,对很多事物不再是从前的感觉和看法,所以在我的笔下,诗风、文风也就跟从前不大一样了。多年来,我已不再写那种激昂的政治抒情的作品,也没有《童话》式的唯美的诗句。现在我写诗试图表现的,只是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点感悟。所以,我的诗风比较沉稳,和从前的风格相比,几乎判若两人。这里有很多原因,主要是我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再写,在思想感情上已不可能像青少年时代那么单纯了。”[7]这足以证明诗人重新面对诗歌时无论从心态,还是从情感方面都已经有了崭新的认识,不过,在这种认识中,集中传达的仍然是一种理性化的东西。而完成于这一时期的《秋水篇》、《高速夜行车》以及90年代的《忆昙花一现前后》、《读冯至〈十四行集〉》、《紫色雨》等都是以较为典型的哲理诗、具体象征和寓言的方式以及对生命的深刻感悟与认知,对这种“理性化色彩”进行了具体而外在的表达。
至此,我们在全面联系诗人生活经历的前提下,已经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常常弥漫于绿原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的具体成因了:除了幼年的苦难经历和适应时代性、社会性的外在要求之外,生存背景的强烈转变、炼狱式的生涯、岁月流逝中成熟与坚定都是形成这种理性化色彩的重要原因。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绿原本人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兼备古今中外哲学、历史、文学等多方面知识的事实。于是,所谓的“理性化色彩”便在绿
作者:张立群 回复日期:2007-4-26 14:55:001# 原的诗歌中以多样化、多层次、多角度的方式予以展开了。
二
纵观绿原的诗歌创作历程,可以清楚地发现:所谓的“理性化色彩”大致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表达的。首先,是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写于1948年的《诗与真》虽然在知名程度上无法与后期的一些广为人们传诵的作品相比,但在这首题记为“诗没有技术 真理没有衣服 人没有世故”的短制当中,绿原还是以“诗是人类底兄长/它指责生活底幻想/诗给人以高度的自由/人必须有海水的方向/诗和真理都很平常/诗决不歌颂疯狂//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的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诗歌如何乃至为何寄予理性(或曰诗人对自我诗歌功能)进行了一种形象的表达。而在稍后的《诗人》(1949年)当中,绿原又以“解读诗人”(诗歌内容,见上)本身的方式,对诗歌写作者本身寄予了一种理性的承担。自然,在这种前提下,诗人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就获得了相对稳定意义上的“写作基础”。
如果说当年的“童话”诗歌常常由于天真、明朗和淡淡的哀伤而掩盖了诗人心中童年的苦难经历,那么,炼狱时期的绿原已经将诗歌中的“理性”暴露的一览无遗。以著名的《又一名哥伦布》为例,在这首写于囹圄时期的作品之中,绿原通过古今中外的对比与象征,将自己比喻为500年前航海探险的哥伦布。然而,对比当年乘坐“圣玛丽娅”号航船、在空间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行进的哥伦布,今天的“哥伦布”却是以单身牢房为孤独的“圣玛丽娅”在时间的航线上“没有分秒,没有昼夜”——
这个哥伦布形削骨立
蓬首垢面
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
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
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
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
坚信前面就是“印度”——
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
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哥伦布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虽然,“他终于没有到达印度/却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然而,今天中国式的“哥伦布”却只能凭借着“常识”和“坚信”去寻找“新大陆”。诗结尾处的“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已经清楚地说明这个代表真理与目的的“新大陆”在当时是无法获得任何承诺的。不过,正是这样一种可以坚定信念的意志,却使诗人当时的艰难处境、忧患意识以及透过诗歌可以体验到的宽广意境得到了深刻的表达。
《重读〈圣经〉》是绿原在这一时期另外一篇重要的作品。在这首可以与《又一名哥伦布》并称为“双璧”的诗中,绿原以“‘牛棚’诗抄第n篇”的别样自诩和借喻的方式,将《圣经》神话故事与现实高度融合在一起:
今天,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
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
今天,马丽娅马格达莲注定永远蒙羞,
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
这时“牛棚”万籁俱寂,
四周起伏着难友们的鼾声。
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
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
“到了这里一切希望都要放弃。”
无论如何,人贵有一点精神。
我始终信奉无神论:
对我开恩的上帝——只能是人民。
整首诗不但笔力沉重、深刻犀利,而且,又在不失明朗、乐观的情怀中浸透了诗人对人生、世道的深入思考,因而,其本身投射出来的厚重感、批判意识以及自觉的理性思辨色彩,也就在同类作品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者:张立群 回复日期:2007-4-26 14:59:002# 与强烈理性思辨色彩相对应的是绿原诗歌中的哲理化倾向和知识化倾向。哲理化色彩以及知识化色彩是绿原诗歌的另一显著特征,同时,也可以视为是理性化色彩的又一外在表现。当然,所谓哲理化倾向往往由于其含义的原因而具有内在的层次感。在《绿原论》一文中,陈丙莹曾这样论述道:“有的论者认为哲理化是绿原诗歌的致命伤。事实上恰恰相反,绿原政治诗的独创性正在于他把哲理的艺术引入革命诗、新诗。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哪一个诗人如绿原这样重视哲理,大量地运用哲理,如此成功地把哲理诗化。”[8]确然,浸透于绿原诗中的哲理由于时代语境和诗人个性特点的原因,并非是那些现代玄学派的沉思与默想,而是融合社会现实、革命哲学的以及生命体验的一种理性发挥。比如,在绿原闻名一时的政治抒情诗中,读者不但可以能够体会到情感的激越,而且,还能在同时得到一种思索的激发。因而,这种融合情感、但又并非裸露理念的作品,就并不仅仅是写出了人生的哲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以激动人心的方式,让读者在阅读与思考中通向诗的哲理。
在绿原诗歌哲理化表征的过程中,常常时隐时现于诗人作品中的宗教意识以及宗教情怀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已经在《重读〈圣经〉》等作品中发现了绿原的宗教情怀(如巴巴拉•霍斯特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耶稣》中“关于绿原的《重读圣经》”的论述),而反复在作品中出现宗教人物、宗教题材、宗教色彩,在绿原的诗歌中也并非只占领少数地位。但在这些诸如“晚祷”、“十字架”等意象、类似以诗解读宗教故事的篇章,以及诗人在受难之后于炼狱环境下写出的大量作品中,最终与宗教救赎相关的却是如何思考现实的社会人生与永恒的真理。比如,在《伽利略在真理面前》(1946年)这个与“中世纪教会”密切相关的作品中,诗人的最终目的是要引申到现实中的“政治犯”、“人的标准”以及对真理的追求。所以,这些所谓的宗教意象到最后也就成了一种表达哲理化倾向的“符号象征”,并在狂飙似的政治理性冷却下来之后,转化为一种特定哲学理性的物质承担。
同样地,知识化倾向在绿原诗歌的“理性化色彩”当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里所谓的“知识化”并非就是简单指向绿原大量阅读之后,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的知识性倾向,它在某种程度还指代绿原诗歌接受的诗学影响乃至师承关系。早在考察建国之前绿原诗歌的创作过程时,有论者便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与歌德性格的重叠,便代表了绿原追求的最重要的方向”[9],而生性好学和受难之后自我排遣时的阅读与补充,也无疑为这种知识性的写作素养创造了“客观的条件”。因而,在后来的《歌德二三事》、《西德拾穗录》、《秋水篇》等作品中,俯仰古今,熔哲学、历史、文学于一体,不但表现出一种更为深远的境界,而且,还常常在个性气质、知识融合的过程中,传达或曰加重了诗人诗歌原来就存有的“理性化色彩”。或许正因为如此,熟悉绿原诗歌创作的友人才会进行如下的评价:“如果说,解放初期新诗歌创作中那种缺乏艺术感染力的空洞歌颂,与他诗创作上潜伏的理念化倾向容易不自觉地合拍起来;那么他后来多年在孤独中被迫冷静思考问题的经历,他从事文艺理论翻译的习惯,以及他的诗作固有的冷峻的论辩性质,更从诗人主观上助长了那种理念化的倾向。” [10]
最后,融形象、情感于一体也是绿原诗歌“理性化色彩”的重要特征。强调“理性化色彩”的诗歌往往由于侧重理性的表达,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诗歌的情感与具体的形象。但是,如果一旦形象和情感过度的得以放逐,则会使诗歌的说理变得生涩、干枯。绿原是一位善于处理诗歌情、理以及形象的诗人。他不但常常通过非凡的想象设造哲理的具体形象与象征,同时,熟识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也造就了他诗歌中可以以诸多知识化形象来拓展了联想的广度和深度,而且,绿原的许多成功的哲理诗也并不晦涩。
与以形象说理相一致的还有绿原诗歌中浓郁的抒情性。许多研究者都曾经注意到绿原一生很少写过情诗,然而,这并不是诗人缺乏抒情的依据与理由。事实上,从“童音”时期开始,绿原的诗歌就已经表现出了坦诚而率真的抒情性;政治抒情诗时代的绿原更是以浓郁的感情色彩、尖锐有力的讽刺,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黑暗社会的愤怒发挥到了极致。只不过,绿原很快由于所谓的“反动集团”而被陷入了逆境,于是,其情感的抒发也相对变得内敛,其形象表达也显得相对深沉。但是,这样的现实条件也造就了绿原诗歌理性表达的均衡性。在《又一名哥伦布》、《重读〈圣经〉》等篇章里,生动感人的形象与深刻哲理、内蕴的情感相互契合所产生的力量是动人心魄的。而自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呈现在绿原诗歌中那种近乎超然的心态、深刻的理性则正是这种多重结合在岁月淘洗下的自然延伸。
正如绿原在一部诗集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诗人是在生活之中,不是在舞台之上。生活远比舞台更宽广,更严峻,更难通向大团圆的结局。因此,诗人只能够、也只应该按照生活的多样化的本色,来进行探险式的创作,而不能是,也不应是舞台上常见的、用一种程式向观众展示一段既定人生的表演艺术家。”[11]贯穿于绿原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艺术的执着、岁月的坚定等多方面因素共同熔铸的结果。虽然,绿原并没有以理论和口号的方式宣扬过自己的诗歌追求,但对诗歌理性的真善美追求却始终伴随着他的创作实践,并在时光延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他的生命并进而成为其生存的重要方式。因此,无论就三言两语就能启发读者的心智,还是诗人本身将诗歌视为崇高而神圣的事业,都是其艰难、孤独但又不乏自信的诗歌旅程的必然结果。“但诗不能有庸俗的胜利/理想和果实最后总归可能”,绿原诗歌的理性化色彩是血肉熔铸后的一次结晶,而熔铸过程中的执着则是引人瞩目的一次心路历程。
注释:
[1]牛汉:《荆棘与血液——谈绿原的诗》,《学诗手记》,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74页。
[2]周良沛:《绿原的诗》,《诗刊》,1992年2期。
[3]关于绿原接受现代派特别是卞之琳诗歌的影响,具体可见《人之诗》的“自序”部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罗惠:《我写绿原》,《新文学史料》,1983年2期的部分介绍。
[4]出处同[1],70页。
[5][9]李怡:《从“童真”到“莽汉”的艺术史价值——绿原建国前诗路历程新识》,《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5期。
[6]关于绿原诗歌四个时期的具体划分以及每一个时期的诗歌特点,具体可见刘扬烈:《诗神•炼狱•白色花——七月诗派论稿》中的“第十二章 绿原论”,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7]见《刘士杰访绿原》,2004年10月19日下午。
[8]陈丙莹:《绿原论》,《抗战文艺研究》,1987年2期。
[10]牛汉:《荆棘与血液——谈绿原的诗》,《学诗手记》,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74~75页。
[11] 绿原:《〈人之诗〉续编》“序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