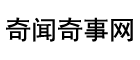四月的纪念是谁写的?
原文:四月的纪念刘擎 王嫣二十岁,我爬出青春的沼泽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六弦琴黯哑在流浪的主题里你来了我走向你用风铃草一样亮晶晶的眼神你说你喜欢我的眼睛擦拭着我裸露的孤独孤独,为什么你总是孤独真的真的吗?第一次第一次吗?太阳暖融融的手指轻轻的暖融融的 轻轻的碰着我了碰你了吗?于是往事再也没有冻结愿望往事再也没有冻结愿望我捧起我的歌,捧起一串串曾被辜负的音符我捧起我的歌,捧起一串串曾被辜负的音符走进一个春日的黄昏一个黄昏,一个没有皱纹的黄昏和黄昏里不再失约的车站不再失约,永远不再失约四月的那个晚上没有星星和月亮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那个晚上很平常我用沼泽的经历交换了你过去的故事谁都无法遗忘,沼泽那么泥泞故事那么忧伤这时候你在我的视网膜里潮湿起来我翻着膝盖上的一本诗集,一本惠特曼的诗集我看见你是一只纯白的飞鸟我在想你在想什么我知道美丽的笼子囚禁了你也养育了你绵绵的孤寂和优美的沉静是的,养育了我也囚禁了我我知道你没有料到会突然在一个早晨开始第一次放飞,而且正好碰上下雨是的,第一次放飞就碰上下雨我知道雨水打湿了羽毛沉重了翅膀也忧伤了你的心是的,雨水忧伤了我的心男:没有发现吗?你在看着我吗?我温热的脉搏正在申请一个无法诉说的冲动真想抬起眼睛看看你可你却没有抬头没有抬头我还在翻着那本惠特曼的诗集也许我并不是岩石并不是堤坝不是岩石也不是堤坝并不是可以依靠的坚实的大树也不是坚实的大树可是如果你愿意你说如果我愿意我会用勇敢的并不宽阔的肩膀和一颗高原培植的忠实的心为你支撑起一块永远没有委屈的天空没有委屈的天空,你说如果我愿意是的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愿意我愿意作者之一刘擎简介:刘擎,1963年出生。1978年就读上海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85年获工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1赴美国攻读政治学,先后获得硕士(马凯大学)与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回到上海工作,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2005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四月的纪念的全诗是什么?
原文:四月的纪念刘擎 王嫣二十岁,我爬出青春的沼泽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六弦琴黯哑在流浪的主题里你来了我走向你用风铃草一样亮晶晶的眼神你说你喜欢我的眼睛擦拭着我裸露的孤独孤独,为什么你总是孤独真的真的吗?第一次第一次吗?太阳暖融融的手指轻轻的暖融融的 轻轻的碰着我了碰你了吗?于是往事再也没有冻结愿望往事再也没有冻结愿望我捧起我的歌,捧起一串串曾被辜负的音符我捧起我的歌,捧起一串串曾被辜负的音符走进一个春日的黄昏一个黄昏,一个没有皱纹的黄昏和黄昏里不再失约的车站不再失约,永远不再失约四月的那个晚上没有星星和月亮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那个晚上很平常我用沼泽的经历交换了你过去的故事谁都无法遗忘,沼泽那么泥泞故事那么忧伤这时候你在我的视网膜里潮湿起来我翻着膝盖上的一本诗集,一本惠特曼的诗集我看见你是一只纯白的飞鸟我在想你在想什么我知道美丽的笼子囚禁了你也养育了你绵绵的孤寂和优美的沉静是的,养育了我也囚禁了我我知道你没有料到会突然在一个早晨开始第一次放飞,而且正好碰上下雨是的,第一次放飞就碰上下雨我知道雨水打湿了羽毛沉重了翅膀也忧伤了你的心是的,雨水忧伤了我的心男:没有发现吗?你在看着我吗?我温热的脉搏正在申请一个无法诉说的冲动真想抬起眼睛看看你可你却没有抬头没有抬头我还在翻着那本惠特曼的诗集也许我并不是岩石并不是堤坝不是岩石也不是堤坝并不是可以依靠的坚实的大树也不是坚实的大树可是如果你愿意你说如果我愿意我会用勇敢的并不宽阔的肩膀和一颗高原培植的忠实的心为你支撑起一块永远没有委屈的天空没有委屈的天空,你说如果我愿意是的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愿意我愿意作者之一刘擎简介:刘擎,1963年出生。1978年就读上海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85年获工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1赴美国攻读政治学,先后获得硕士(马凯大学)与博士(明尼苏达大学)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回到上海工作,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助理。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2005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谁知道这首诗?
在本世纪初那几年里,耐夫斯基大街上的一家旅行社展出了一辆三英尺的棕色国际卧车模型。它做得惟妙惟肖,远胜于我那辆涂锡的玩具火车。但可惜它是非卖品。人们可以想象出它天蓝色的内壁、车厢墙壁上皮制的浮雕图案、光滑的嵌板、嵌入墙中的镜子、郁金香形状的台灯,以及其他令人心驰神往的细节。宽窗和窄窗交替排列,或单或双,其中有些是用磨花玻璃制成的。在许多隔间里都备有床铺。
那时曾显赫一时的“诺尔快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就再也不是老样子了)一律由这样的国际列车组成。它联结彼得堡和巴黎,一周两班。其实这本是直达巴黎的车,如果不是乘客必须要在俄国和德国的边境(维尔兹波洛夫——埃德特库嫩)换乘一辆外表大致相似的列车,因为在那里,俄国式的64.5英寸缓慢的宽轨要改换成56.5英寸的欧洲标准轨,而且煤取代了桦木。
在我脑海深处,我至少还能记起五次这种去巴黎的旅行,终点是里维埃拉或比亚里茨①。我现在想起那次是一九〇九年,那时我的两个妹妹被留在家里由保姆和姨妈照管。我父亲戴着手套和旅行帽正坐在他和家庭教师合住的一个隔间里读书。我和弟弟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洗手间。母亲和女仆住在我们隔壁。我们一行人中比较古怪的,是父亲的男仆奥西普(十年之后,迂腐的布尔什维克把他枪杀了,因为他占用了我们家的自行车没有上缴国家),他带了一个陌生人与他同行。
那年四月,皮尔里已经到了北极。五月,恰里亚平已经在巴黎演唱了。六月,美国国防部被有关改良的新型“齐柏林飞艇”②的传闻弄得焦虑不安,于是告诉记者他们计划建立空中海军。七月,布莱里奥③从加来飞到多佛(他迷失方向时,多走了一段冤枉路)。那时是八月末,俄国西北部的冷杉和沼泽在车窗外掠过,第二天就变成了德国的松树沙地和石楠。
我和母亲在一张折叠桌上玩一种叫“杜拉契基”的扑克牌游戏。虽然是大白天,我们的牌、杯子和放在别的架子上面的箱子的锁仍然映在车窗上。于是玻璃中那些虚幻的赌徒随着列车一道穿越森林和田野,在深谷中、在飞驰的农舍中不停地出牌、下注。
“Ne budet-li,li ved’ustal(玩够了吗?你不累吗)?”母亲问过之后,便一边慢慢地理牌,一边陷入沉思。隔间的门开着,我能看见过道的窗户,那里的电线——六根黑色的细电线——尽管闪电似的打击通过一根接一根的电线杆对付它们,它们总能尽全力斜过来,朝天上爬去。但是正当这六根线微微得意洋洋,处于成功的波线形即将到达窗顶时,特别猛烈的一击就又把它们打下去,打到最低点,于是它们只得重新开始。
在这样的旅行中,当我们穿过德国的一些大城镇时,火车会放慢车速,差不多是徐徐掠过房屋正面和商店招牌。这时我经常会感到双重的兴奋,甚至比到达终点站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看到一座城市与它那玩具般的电车、椴树和砖墙进入到隔间里,热热闹闹地占满镜子,还占满过道里的窗户。火车与城市之间这种熟不拘礼的关系正是让人激动不已的一方面。另一种兴奋是把我放在一个过路人的位置上,我想象他会像我一样感动地看着那长长的、富于浪漫情调的棕色列车,其车厢之间的帘幕像蝙蝠翅膀一样乌黑,车厢上的金属字在斜阳中闪烁着铜光,它不慌不忙地在平淡无奇的大道上筑起一座钢铁桥梁,然后当所有车窗一下子亮起灯时,列车绕过了最后一幢房舍。
但是这些五光十色的景象也有一些缺陷。车窗宽阔的餐车、一排晶莹剔透的矿泉水瓶子、斜折的餐巾、摆样子用的巧克力(其包装纸——尽管写着“凯耶”、“科勒”等等牌子——里面包着的巧克力却味同嚼蜡),乍一看就像置于一条摇摇晃晃的蓝色走廊之外的凉爽港湾;但是当最后一道菜端上来时,人们会不断注意到列车以及在颠簸的车上步履踉跄的侍者等,都被胡乱地淹没于周围的风景中了,而车外的景色却自己完成了一套复杂的运动系统,白天的月亮始终与人们的盘子保持同一高度;远处的草地像扇子一样铺开;近处的树木踏着无形的节奏吹向铁道,一条平行的铁轨突然并接而自杀,一长条草地,上升,上升,直到混合速度的小见证人被迫吐出他那部分的草莓果酱炒蛋。
然而,只有在夜晚,“欧洲快车与货运国际公司”这个名字中的魔力才闪现出来。我的床在弟弟睡铺下面(他睡着了吗?他是否在那里?),在半黑的隔间里我从床上看到完整或不完整的物体和影子小心地来来去去,不知所向。木制品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通向洗手间的门附近,衣钩上挂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上衣,再往上是蓝色夜灯发出的两道微光,在有节奏地摇摆着。很难把这种停滞的感觉和诡秘的栖息与车外飞掠过去的夜色联系在一起,而我知道,它确实在飞掠过去,星火闪烁、难以辨认。
我只要把自己想像成火车司机就可以入睡。当我把一切都安置得井井有条时,一种满足的困倦就会袭上来——无忧无虑的乘客在车厢里享受着我带给他们的旅行,他们抽着烟,相互微笑致意、点头、打瞌睡;侍者和厨师以及列车上的警卫(我得把他们安置好)正在餐车里痛饮;而我自己瞪大眼睛,浑身沾满灰尘,看着机车外慢慢变细的轨道,看着黑乎乎的远处像红宝石或绿宝石一样的亮点。随后,在睡梦中我会看到迥然不同的东西——一架大钢琴下面滚动着的玻璃弹子,或者一辆打翻在地、但轮子仍在不停转动的玩具火车。
车速的改变有时会打断我流畅的睡眠。灯光慢慢从窗外掠过;每盏灯过处,窗口这块空隙都会被仔细检查,然后一块夜光罗盘就会测量那些阴影。过了不久,火车就会在西屋公司生产的引擎发出的一声长叹中停下来。有什么东西从上面的床上掉下来(第二天发现是我弟弟的眼镜)。由于窗帘被上铺的床沿挡住了,它只能拉下一半,所以我得拖着被单来到床脚处,以便小心翼翼地解开窗帘所带来的搭扣,这真叫我无比兴奋。
灰白的蛾子围着一盏孤灯打转,就像卫星绕着木星一样。一张撕开的报纸在凳子上搅动了一下。列车里的某个地方传来一种被捂住的声音,那是有人在不适地咳嗽。我面前这片站台上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但我还是不忍离去,直到火车开动,它自己离去为止。
第二天早上,远处湿地上沿一条沟生长着奇形怪状的柳树或一排白杨,中间被一道乳白色的雾隔开,有人说火车正驶过比利时。火车于下午四点抵达巴黎;即使只停留一夜,我也总有时间买些东西,比如一个黄铜制、外面裹着一层粗银漆的小埃菲尔铁塔。第二天中午我们登上“南方快车”,在开往马德里的路上,晚上十点左右我们在离西班牙边境只有几英里、比亚里茨的拉内格莱斯站下了车。
二
当年,比亚里茨仍保持着它的本色。灰蒙蒙的黑莓丛和杂草丛生的待售的土地紧挨着通向我们别墅的路。卡尔顿尚在建造之中。三十六年后,陆军准将萨缪尔·麦克劳斯基才占领了皇宫旅馆里的皇家套房,这家旅馆坐落于从前一所宫殿的原址上。后来在六十年代,据说有人曾看见那个异常敏捷的巫师,凡尼尔·休姆,就在那个宫殿原址处,正用一只赤脚(模仿一只鬼手)抚弄着尤金妮皇后那张善良、诚实的脸。在赌场附近散步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卖花女涂着眉、满脸堆笑,截住一位散步者,将石竹花饱满的花托灵巧地插进他的扣眼里。当他侧过头俯视这朵插花时,他的左下颌突现出一种皇室特有的褶痕。
沿着黑色的海岸线,排列着各式各样的海滨躺椅和长凳,许多父母坐在那里,他们那些戴着草帽的孩子正在前面沙滩上玩耍。人们看到我跪着,正试图用一只放大镜点燃一把捡到的梳子。男人夸耀着他们的白裤子,而这些裤子在今天看来就彷佛洗后缩了水一样可笑。在那个季节里,女士们身穿丝绸面料的轻便外衣,戴高筒宽檐的帽子和满是绣花的白面纱,穿前面镶褶边的罩衫,花边垂在她们的手腕上,也垂在她们的阳伞上。微风吹得人口干舌燥。一只迷途的金黄色蝴蝶急匆匆飞过喧闹的海滨。
还有小贩们走来走去,高声叫卖,兜售花生、包糖的紫罗兰、绿色果仁冰淇淋、口香糖块以及从一只红桶里拿出的又干又硬、像维夫饼干一类的表面凸起的大块东西。我看见卖饼干的人背着沉重的桶,弯着腰在深深的白色沙滩上艰难地行走,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一旦有人叫住他,他就把皮带子扭开,将肩上的桶卸下来,让它重重地落在沙地上,其姿态就像比萨斜塔一样。他用袖子擦脸,然后用桶盖上的数字摆成圆盘投标游戏。标盘吱吱地旋转着。幸运的人能够投中价值一个苏的饼干。但是命中的数越大,我就越为他感到难过。
洗海水浴是在海滨的另一部分进行。职业泳手是些身穿黑色泳衣、强健的巴斯克人,他们正帮助女人和孩子享受海浪的凶猛。这种浴场仆役会扶你背冲着将要冲上来的海浪,当汹涌澎湃的绿色海水带着泡沫从身后轰然而至,猛烈地撞击你,将你击倒时,他们会握住你的手。跌倒几次之后,像海一样闪着光的浴场仆役会把喘息不定、浑身发抖,而且呛了水的顾客引到平坦的岸上,然后一位下巴上满是灰色的令人难忘的老妇人会从挂在衣架上的几件浴衣中迅速选出一件来。在一间安全的小木屋里,另一位侍者会帮你脱下湿透的、沾满沙子的泳衣。它会啪的一声脱落至木板上,而还在浑身打颤的你便会从泳衣里跨出来,踩在它蓝色、铺散开的条纹上。小木屋里散发着松木的香味。长满皱纹的驼背侍者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水,你可以把脚浸在里面。从他那里我知道在巴斯克语中“蝴蝶”是“misericoletea”,至少听起来是如此(我在字典中找到七个词,最接近的一个是“micheletea”),这一切都一直存在我记忆的玻璃盒里。
三
有一天,我在海滨深棕色、比较潮湿的地方挖泥玩儿,低潮时那里的泥最适合垒城堡,紧挨着我身边是一个法国小女孩,她叫科莱特。
她到十一月十岁,而我四月份就已经十岁了。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到一块参差不齐的紫色贝壳上,这是她光着她那长着细长脚趾的脚正好踩到的。不,我不是英国人。她轮廓分明的脸上满是雀斑,因此她绿色的眼睛似乎也斑驳闪亮。她穿着现在被称为游乐装的衣服,这包括一件袖子挽着的蓝色紧身上衣和一条蓝色针织短裤。一开始我把她当成了男孩子,可后来她纤细手腕上的手镯和从她海员帽上垂下的棕色螺旋状鬈发弄得我迷惑不解。
她说话很快,嘁嘁喳喳像小鸟一样,混杂着家庭教师教过的英语和巴黎腔法语。两年前,也是在这片海滨上,我曾深深迷恋上一位塞尔维亚医生可爱的、晒得黝黑的小女儿;但当我见到科莱特时,我马上意识到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科莱特似乎比我在比亚里茨偶然遇到的其他玩伴都奇异得多。不知怎么,我有种感觉,那就是:她不如我快活,也不如我那样受宠爱。我之所以这样猜想是因为看到她娇嫩、轻柔的小臂上有一块伤痕。“他拧起人来和妈妈一样狠,”她说,说的是一只蟹。我想过各种各样的计策,想把她从她父母那里救出来。我曾听人轻轻耸肩对妈妈说过,她父母是“巴黎的资产阶级”。我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种轻蔑,因为我知道那些人都是驾着他们的蓝色和黄色豪华汽车一路从巴黎驶来的(这在当时是一种时髦),却让科莱特和她的狗以及家庭女教师毫无光彩地乘普通客车而来。她的狗是一只母狐狸狗,脖子上挂着铃铛,屁股总是扭来扭去的。它精力旺盛,总是舔科莱特玩具桶外面的咸海水。我还记得画在桶上的船、落日和灯塔,但我记不起狗的名字了,这叫我烦恼。
在比亚里茨逗留的两个月中,我对科莱特的感情几乎要超过我对蝴蝶的热爱了。因为我父母不大喜欢碰上她家父母,所以我只能在海边见到她;不过我常常想着她。如果我看见她在哭,我就会感到一种无助的痛苦,这也会让泪水涌入我的眼眶。我无法消灭那些叮咬她柔软脖颈的蚊子,但我可以、而且确确实实为她打赢了一架,对手是一个待她粗野的红头发男孩。她经常给我一把温乎乎的硬糖。有一天我们一起弯着腰看一条海星,科莱特的鬈发蹭到了我的耳朵,她突然转过头吻了我的面颊。我当时实在是太激动了,我所能想到说的只是这么一句:“你这个捣蛋鬼!”
我有一枚金币,我觉得这足够我们私奔了。我要带她去哪儿呢?西班牙?美国?还是波城④上面的山里?“在那里,在那里,在山里,”这是我听卡门的歌剧里唱的。在一个奇怪的夜晚,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听着海水循环往复的拍击声,计划着我们的出逃。大海似乎在黑暗中上升、摸索,随后又沉重地朝下倒去。
关于实际的出走,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的记忆依旧保存着这一幕:在一个帐篷的背风处,她顺从地穿上系带的帆布鞋,而我正将折叠好的蝴蝶网塞进一个棕纸袋里。另一幕是:为了躲避追踪,我们进了赌场附近的一架漆黑的电影院(赌场当然是不许进入的)。我们手拉着手坐着,中间隔着狗,它的铃铛时不时在科莱特脚上响动。正放映的是在圣赛巴斯蒂安举办的一场斗牛比赛,画面乱哄哄的,不太清楚,但令人兴奋不已。我记忆中最后一幕是:我的老师领着我沿海滨人行道走着。他长长的腿动起来令人讨厌地轻快,我能看见他紧咬的颌骨肌肉在他紧绷绷的皮下跳动。我那戴眼镜、九岁的弟弟,正巧被老师的另一只手拉着。他不断地往前跑几步,然后像一只小猫头鹰一样,带着充满敬畏的好奇心偷看我。
离开比亚里茨之前所得到的无关紧要的纪念品中,我最喜欢的不是用黑石做的小牛,也不是能发出轰响的贝壳,而是现在看起来几乎充满象征意味的东西——一个海泡石笔架,在其装饰部分有一个小小的水晶窥视孔。你可以把它拿起来靠近一只眼睛,然后眯起另一只,当你的眼睫毛不再闪动时,你能在里面看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画面:有海湾,还有一直伸向灯塔的一连串峭壁。
现在,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发生了。我回想起笔架和小孔中别有洞天的画面,这又刺激我的记忆力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我再次试图想起科莱特那条狗的名字——对了,沿着那遥远的海滩,走在旧日夜晚粗糙的沙滩上,每个足印都慢慢注满被落日照耀的海水,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它回响着,颤动着:弗罗斯!弗罗斯!弗罗斯!
科莱特回到巴黎时,我们已在巴黎停留了一天,准备踏上回家的旅途。在寒冷的蓝天下,我最后一次在一个鹿园里见到她(我相信这是我们两个人的老师特意安排的)。她用一根短棍滚着铁环,在秋天的巴黎,她身上的一切都那么得体、高雅。她从家庭女教师那里拿出一件离别的礼物,塞到我弟弟手中。那是一盒裹着糖衣的杏仁,我知道这是要给我的。随后她马上就跑开了,滚动着闪光的铁环穿过阳光和阴影,绕着我附近铺满落叶的温泉一遍一遍地跑着。在我记忆中,树叶和她的皮鞋皮手套混在一起,她衣着的某些细节(可能是她苏格兰帽上的丝带,或者是她袜子上的图案)当时让我想起玻璃弹子里面的五彩螺线。我似乎还在握着那一道彩虹,不知道该如何处置它,而她滚着铁环则越来越快地围着我跑;砾石路上低矮的圆形栅栏上交错的拱形在路面上投下影子,而她最后就消失在那些依稀的阴影中了。
① 法国南部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城镇。当地气候温和,海滨风景丰富,是著名的旅游地。
② 德国齐柏林公司制造的硬式飞艇。1900年7月2日它在德国康斯坦茨湖出发作首次飞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齐柏林飞艇执行了巡逻和战略轰炸任务。
③ 法国飞行家,用重于空气的飞行器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海上飞行。1909年7月25日,他驾驶布莱里奥Ⅺ型飞机(装有二十八马力发动机的单翼机)飞越英吉利海峡,从加来到达多佛。这次飞行使他长期享有声誉。
④ 法国西部城市,避寒胜地。
如何朗诵四月的纪念?
根据刘擎先生和王嫣女士《四月的纪念》朗诵原声,孤鸿整理、校核。原文如下:
四月的纪念
作者:刘擎、王嫣
男:二十二岁,我爬出青春的沼泽,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六弦琴,黯哑在流浪的主题里——你来了
女:我走向你
男:用风铃草一样亮晶晶的眼神
女:你说你喜欢我的眼睛
男:擦拭着我裸露的孤独
女:孤独?你为什么总是孤独?
男:真的
女:真的吗?
男:第一次
女:第一次吗?
男:太阳暖融融的手指
女:暖融融的
男:轻轻的
女:轻轻的
男:碰着我了
女:碰着你了吗?
男:于是,往事再也没有冻结愿望
女:于是,往事再也没有冻结愿望
男:我捧起我的歌,捧起一串串曾被辜负的音符
女:我捧起我的歌,捧起一串串曾被辜负的音符
男:走进一个春日的黄昏
女:一个黄昏,一个没有皱纹的黄昏
男:和黄昏里,不再失约的车站
女:不再失约,永远不再失约
男:四月的那个夜晚,没有星星和月亮
女: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那个晚上很平常
男:我用沼泽的经历交换了你过去的故事
女:谁都无法遗忘,沼泽那么泥泞,故事那么忧伤
男:这时候,你在我的视网膜里潮湿起来
女:我翻着膝盖上的一本诗集,一本惠特曼的诗集
男:我看见你是一只纯白的飞鸟
女:我在想,你在想什么
男:我知道,美丽的笼子囚禁了你,也养育了你绵绵的孤寂和优美的沉静
女:是的,囚禁了我,也养育了我
男:我知道,你没有料到,会突然在一个早晨开始第一次放飞,而且正好碰上下雨
女:是的,第一次放飞,就碰上下雨
男:我知道,雨水打湿了羽毛,沉重了翅膀,也忧伤了你的心
女:是的,雨水忧伤了我的心
男:没有发现吗?
女:你在看着我吗?
男:我温热的脉搏正在申请一个无法诉说的冲动
女:真想抬起眼睛看看你
男:可你却没有抬头,
女:没有抬头,我还在翻着那本惠特曼的诗集
男:是的,我知道,我并不是岩石,并不是堤坝
女:不是岩石,不是堤坝
男:并不是可以依靠的坚实的大树
女:也不是坚实的大树
男:可是如果你愿意
女:你说,如果我愿意
男:我会的,我会用勇敢的并不宽阔的肩膀和一颗高原培植出的忠实的心,为你支撑起一块永远没有委屈的天空
女:没有委屈的天空,你说如果我愿意?
男:是的,如果你愿意
合:如果你(我)愿意
《四月的纪念》朗诵
《四月的纪念》
作者:刘擎、王嫣
配乐:《思乡曲》
注意:稿件要熟背,感情要丰富,要有感而发,情景交融。
两个人配合一定要默契、紧凑。
看你自己发挥了~
(男)二十岁,我爬出青春的沼泽
象一把伤痕累累的六弦琴
喑哑在流浪的主题里
你来了
(女)我走向你
(男)用风铃草一样亮晶晶的眼神
(女)你说你喜欢我的眼睛
(男)擦拭着我裸露的孤独
(女)孤独!为什么你总是孤独?!
(男)真的
(女)真的吗?
(男)第一次
(女)第一次吗?
(男)太阳,暖融融的手
(女)暖融融的
(男)轻轻的
(女)轻轻的
(男)碰着我了
(女)碰着你了吗
(男)于是 往事再也没有冻结怨了
(女)冻结怨了
(男)我捧起我的歌
(女)捧起你的歌
(男)捧起一串串曾被辜负的音符
(女)捧起一串串曾被辜负的音符 (男)走进一个春日的黄昏
(女)一个黄昏 ,一个没皱纹的黄昏
(男)和黄昏里不再失约的车站
(女)不再失约,永远不再失约
(男)四月的那个夜晚 没有星星和月亮
(女)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 那个晚上很平常
(男)我用沼泽的经历交换了你过去的故事
(女)谁都无法遗忘沼泽那么泥泞 故事那么忧伤
(男)这时候 你在我的视网膜里潮湿起来
(女)我翻着膝盖上的一本诗集 一本惠特曼的诗集
(男)我看见,你是一只纯白的飞鸟
(女)我在想,你在想什么
(男)我知道,美丽的笼子囚禁了你 也养育了你绵绵的孤寂和优美的沉静
(女)是的
囚禁了我,也养育了我
(男)我知道,你没有料到会突然在一个
早晨开始第一次放飞而且正好碰到下雨
(女)是的
第一次放飞就碰到了下雨 (男)我知道雨水打湿了羽毛
沉重的翅膀也忧伤你的心
(女)是的
雨水忧伤了我的心
(男)没有发现吧
(女)你在看着我吗
(男)我湿热的脉搏
正在升起一个无法诉说的冲动
(女)真想抬起眼睛看看你
(男)可你却没有抬头
(女)没有抬头
我还在翻着那本惠特曼的诗集
(男)是的,我知道
我并不是岩石,也并不是堤坝
(女)不是岩石,不是堤坝
(男)并不是可以依靠的坚实的大树
(女)也不是坚实的大树
(男)可是,如果你愿意
(女)你说如果我愿意
(男)我会的
我会勇敢地以我并不宽阔的肩膀和
一颗高原培植出来忠实的心
为你支撑起一块永远没有委屈的天空
(女)你说,如果我愿意
(男)是的,如果你愿意
(合)如果你/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