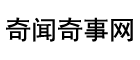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期较为流行的一种讲唱文学(或艺术)。目前学术界对它有一个趋于公认的定义:它是“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调的许多短套联成数万言的长篇,杂以说白,以说唱长篇故事。”(见《辞海》该条)这一定义基本上揭示了诸宫调的结构特征。 只是“短套”之说不够准确,因为现存的诸宫调作品中有一些无“尾”的独立散词。这些独立的散词显然不能称之为“套”,而只能视之为“歌唱单位”。诸宫调是由许多不同宫调的歌唱单位而构成一个艺术整体,杂以说白,以敷演长篇故事。它在形式特点、音乐体制和表演方式等方面与其它古代艺术样式存在明显差异,它的艺术结构是钜鸿的、空前的,因而它具有不可取代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意义。 一、诸宫调的发现 诸宫调兴于北宋中期,为孔三传所创,很快成为瓦肆中一种为人们所喜爱的伎艺。 靖康之变后,诸宫调南北分流。金代诸宫调现存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简称《刘知远》)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两部作品。南宋诸宫调未有完整的作品流传下来,今所见者只有戏文《张协状元》第一出的“副末出场”。 对比起来看,金宋诸宫调存在很大的差别。如在曲式上,金代诸宫调一般是采用一首完整的词入唱,而南宋诸宫调只采用同一词调的上片或下片入唱。 在用韵上,南宋诸宫调依照词律,严辨平、仄、入三声;而金代诸宫调与曲韵相合,入声与平、仄通押。元代初期(至元年间),诸宫调兴盛一时。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简称《天宝遗事》)便是此时的产物。从其残存的曲辞看,已与北曲无多大差别。元贞(公元1295—1296)以后,元杂剧进入兴盛时期,诸宫调开始衰亡。 久而久之,渐渐为人们所陌生。如陶宗仪在《辍耕录》卷二十七中所云:“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词之冗乎?”明清两代,人们已不知诸宫调为何物,以至对《董西厢》的称呼纷纭杂乱。朱权称之为“北曲”(《太和正音谱》),胡应麟称之为“传奇”(《少室山房笔丛》),徐渭称之为“弹唱词”(《北本西厢记题记》),沈德符谓之“院本”(《顾曲杂言》),毛奇龄谓之“弹词”(《西河词话》),梁廷谓之“弦索”(《曲话》)。可见明清时人对诸宫调已茫然不知。 诸宫调徒存其名,其实(作品实体)已被丢失。作品实体被丢失的原因主要在于诸宫调在元杂剧兴盛之后很快衰落下去,作品纷纷佚散。《董西厢》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而由于钟嗣成的《录鬼簿》称之为“乐府”,以致后人不知它为诸宫调作品。虽然王伯成的《天宝遗事》为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指明是诸宫调,但由于只残存曲辞,且已“曲化”,与《董西厢》这部“词体”诸宫调作品存在很大的差异。 当人们以《天宝遗事》为参照时,很难将《董西厢》与诸宫调联系进来。又由于明清的学者所能见到的诸宫调作品只有这两部,无法探寻出诸宫调由“词体”向“曲体”进化的轨迹。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不知《董西厢》为何种艺术作品,只得胡乱揣猜,以至出现如此五花八门的称谓。 直到本世纪初,丢失的诸宫调实体才被找回。 大学者王国维第一个发现《董西厢》就是诸宫调作品。他在1908年成书的《曲录》中仍将《董西厢》与《天宝遗事》并归于“传奇部”,直到1912年才考证《董西厢》为诸宫调作品: 此编(《董西厢》)之为诸宫调有三证:本书卷一《太平赚词》云:“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此开卷自叙作词缘起,而自云在诸宫调里,其证一也。元凌云翰《柘轩词》有《定风波》词赋《崔莺莺传》云:“翻残 金旧日诸宫调本,才入时人听。”则金人所赋《西厢词》为诸宫调,其证二也。此书体例,求之古曲,无一相似。独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所选者大致相同。而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上于王伯成条下注云:“有《天宝遗事》诸宫调行于世。”王词既为诸宫调,则董词之为诸宫调无疑。 ① 王国维的考证是有力的。不久,《刘知远诸宫调》和戏文《张协状元》先后被发现,证明了王国维的判断是正确的。丢失已久的诸宫调作品实体被重新找回,无疑是学术界一件重大的事情,王国维功不可没。从此词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诸宫调研究。王国维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正如郑振铎在《宋金元诸宫调考》中所说:“诸宫调的研究,自当以王氏为开始。” 《刘知远诸宫调》是于1907年至1908年在新疆黑水古城发现的。郑振铎从向达那里获得一部手抄本,后又在赵斐云处见到原书的影片。1932年,郑振铎写成了《宋金元诸宫调考》,奠定了我国诸宫调研究的基础。此后,诸宫调这一艺术样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意。
二、诸宫调的兴起 诸宫调是宋金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说唱体文学形式。它以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短套,首尾一韵,再集合不同宫调的若干短套可以说唱的长篇故事,因此称为“诸宫调”。
诸宫调兴起于北宋民间。根据宋人王灼《碧鸡漫志》的记载,北宋熙宁至元祐年间,泽州(今山西晋城)人孔三传首创诸宫调,用以说唱传奇故事。宋、金诸宫调的题材相当广泛,涉及烟粉、灵怪、神话、历史等内容。
《西厢记诸宫调》是迄今惟一保存完整的诸宫调作品,标志着当时说唱文学的水平。 三、诸宫调首创地 宫,是我国古代各种音阶中的第—级音,以宫作为音阶起点的曲子称为宫调。由多种宫调组合成—个完整的长曲,就是诸宫调。它最早是在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创立的。 约在北宋神宗熙宁至哲宗元年间,山西晋城(时称泽州)艺人孔三传来到文艺演出百花竞放的东京,最先创造了诸宫调。其表现形式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说的部分为白话散文,唱的部分就是按不同宫调曲谱规格创作的韵文,音乐上吸收了前代乐曲及宋代民间小调的精华。伴奏可少可多,可以是一两件小乐器,也可以是由多种乐器组成的乐队。 《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一书中列举的诸宫调着名演员,第一个就是孔三传,此外还有耍秀才。《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一节中清楚地说明了它的源处:“诸宫调本京师(开封)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这一新颖活泼的文艺样式,不论是在瓦子勾栏,还是在达官贵人的府第,都很受欢迎。可惜当时的作品没有被流传下来。
诸宫调在宋都东京创立后,不但使整个宋代说唱曲艺艺术更加多姿多彩,而且影响波及到后世戏曲。元杂剧的形成直接受诸宫调影响,就是从现代戏曲和许多说唱结合的曲艺节目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诸宫调的影子。
四、西厢记诸宫调 金文学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西厢记诸宫调》的出现。
《西厢记诸宫调》作者董解元,主要活动于金章宗(1190—1208在位)时期(见《录鬼簿》和《辍耕录》),“解元”是当时对士人的泛称。名字不详。汤显祖评本《董西厢》说他名朗,但不知何据;所谓“汤显祖评”,似也出于伪托。唯董解元在作品开头部分曾作过一些自我介绍,尚可略见其为人:
“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教惺惺浪儿每都伏咱。
不曾胡来,俏倬是生涯。”“携一壶儿酒,戴一支儿花;醉时歌,狂时舞,醒时罢。每日介疏散,不曾着家。放二四,不拘束,尽人团剥。”“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
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余。
诸宫调是一种兼具说、唱而以唱为主的曲艺。因其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而得名。据《碧鸡漫志》等书记载,北宋已有诸宫调;但有完整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则以《西厢记诸宫调》为最早。
《西厢记诸宫调》的故事源于唐传奇《莺莺传》。至宋代有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将《西厢》故事改变成说唱,但在情节上并无改动。只是《莺莺传》结尾肯定张生抛弃莺莺的行为,在《商调蝶恋花》中则把二人的乖离作为悲剧处理,故其结尾云:“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新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这比起《莺莺传》来,是一种进步。至于在具体描写上,虽也略有发展,但未能脱离原来的框架。如写张生与莺莺初见,《莺莺传》是:莺莺起初不肯相见,“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
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商调蝶恋花》则是:“锦额重帘深几许,绣履弯弯,未省离朱户。强出娇羞都不语,绛绡频掩酥胸素。黛浅愁深妆淡注,怨绝情凝,不肯聊回顾。媚脸未匀新泪污,梅英犹带春朝露。
与此相较,《西厢记诸宫调》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但变张生的抛弃莺莺为二人终于结合,而且将张生改成了一个忠于爱情、得不到莺莺宁可自杀的青年,莺莺也改变了原作中的纯粹被动的性格,被赋予了一个由被动演变为主动的过程,最终也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殉于爱情。红娘在原作中是个次要的角色,在《西厢记诸宫调》里却成为很活跃的人物。莺莺的母亲在原作中只起了介绍莺莺与张生相见的作用,对他们的爱情从未加以干涉,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却成为阻碍崔、张结合的礼教的代表,从而使整个作品贯穿了礼教与私情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作的面貌。
从艺术形式和技巧来看,《莺莺传》原作只有三千余字,《诸宫调》却成了五万余字,大大地丰富了原作的情节。其中的张生闹道场,崔、张月下联吟,莺莺探病,长亭送别,梦中相会等场面都是新加的;并随着这些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对喜欢情节曲折的读者来说,这也就更增加了兴趣。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
具体说来,《西厢记诸宫调》在以下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作品对爱情和礼教的矛盾冲突作了着力铺叙,并以爱情的战胜而告终。这主要是通过莺莺的性格发展而体现出来的。
在作品里,张生固然苦恋莺莺,莺莺也很快对他产生了好感。在两人初次邂逅相逢后,“是夜月色如昼,生至莺庭侧近,口占二十字小诗一绝。其诗曰:‘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就依韵和了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可见她已经被打动了。接着,孙飞虎作乱,崔夫人为求张生救援,把莺莺许给了张生。但乱定之后,崔夫人又以莺莺在这以前已许给其内侄郑恒为理由,只让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处。对此,莺莺是不满的,但迫于母亲治家严切,只好隐忍。作者写她在当时听张生自述其情后的心理活动说:“张生果有孤高节,许多心事向谁说?眼底送情来,争奈母亲严切。空没乱,愁把眉峰暗结。
多情彼此难割舍,都缘只是自家孽。……”(《双调·月上海棠》)后来,她在窗外听张生弹琴,深受感动,“不觉泣下”,不料张生开出门来想要抱她。这使得深受礼教熏陶的莺莺感到害怕甚至屈辱。她想找个人向张生说明这一切,让他知道两人不能成为眷属。但她又为此而痛苦难眠。她当时的这一段内心独白很能表现礼教对其爱情火焰的抑制:
奈老夫人情性,非草草。虽为个妇女,有丈夫节操。俺父亲居廊庙,宰天下,存忠孝。妾守闺门,些儿恁地,便不辱累先考。所重者,奈俺哥哥由未表,适来恁地把人奚落。司马才,潘郎貌;不由我,难偕老。怎得个人来,一星星说与,教他知道。(《中吕调·鹘打兔》)
她还没有找到个可以向张生“一星星说与,教他知道”的人,张生却又通过红娘送来了一首诗,其中有“乐事又逢春,花心应已动。幽情不可违,虚誉何须奉”等语。原本所受的礼教熏陶使她认为这是淫诗,对之又怒又怕。“拆开读罢,写着淫诗一首。自来心肠,更读着恁般言语,你寻思怎禁受?低头了一饷,把庞儿变了眉儿皱,道‘张兄淫滥如猪狗,若夫人知道,多大小出丑。’……”(《仙吕调·绣带儿》)于是,她写了一首诗,把张生骗进来,狠狠训斥了一顿。张生受此打击,生了重病,眼看就要死去。莺莺见了这种情景,被她自己用礼教压制下去的爱情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她“愁入兰房,独语独言,眼中雨泪千行。良久多时,喟然长叹,低声切切唤红娘,都说衷肠。道‘张兄病体匡羸,已成消瘦,不久将亡。都因我一个,而今也怎奈何?我寻思:顾甚清白?救才郎!’”(《中吕调·古轮台》)至此,她终于决定为了爱情而背叛礼教。其后崔夫人因莺莺与张生已私下成就姻缘,怕家丑外扬,不得不同意他们结合,乃是爱情的进一步胜利。但如没有莺莺跨出勇敢的第一步,崔夫人当然不会向他们妥协。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私情作为礼教(及其体现者封建家长)对立面而着力加以铺叙的,实以《西厢记诸宫调》为最早。在这以前,例如《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刘兰芝虽也受礼教及封建家长的迫害而离异、死亡,但他们是夫妇而非私情;又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益,虽以不敢违背母亲之命而与别的女子订婚并抛弃霍小玉,但他对霍小玉如此绝情却是自己负心,作品着力铺叙的主要是这种负心行为带给霍小玉的痛苦而非私情与礼教的冲突。至于《莺莺传》所写的崔、张私情,尽管在性质上是违反礼教的,但在作品中礼教始终并未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干涉。而且,张生本可通过媒聘而正式娶莺莺为妻,当红娘提出此点时,张生回答说:“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足见他也并未否定正式婚娶的可能性,只不过等不得“三数月”时间罢了。但在偷情后,他就不再提起与莺莺正式结合的事了,尽管莺莺向他提出:“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他也不予理睬。所以,唐传奇《莺莺传》实在也并未铺叙私情与礼教的矛盾冲突。同时,《西厢记诸宫调》在铺叙这一点时,还显示出了礼教在这方面的不合理性:在崔夫人根据礼教而不准崔、张结合(因莺莺在此之前已许配郑恒)时,他们两人都感到痛苦;在莺莺屈从礼教而拒绝张生时,带给两人的也是痛苦;但当两人终于冲破礼教束缚结成私情时,两人都感到了莫大的快乐。所以,作品的基本倾向乃是赞美私情而背离礼教。这以后,中国的戏曲、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同类型的作品,如元杂剧《墙头马上》、《拜月亭》、王实甫《西厢记》,小说《娇红记》等;而考其源流,实以《西厢记诸宫调》为最早。
其次,作品努力于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刻画。
中国在这以前的叙事文学,无论为写实的或虚构的,都重在事实的描绘;人物的思想感情只是在描绘事实的过程中作为次要的部分来加以交代。抒情文学如诗词等虽重视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但因重视凝炼,又与生活中的本来形态有较大距离。而在《西厢记诸宫调》中,不仅处处以大量篇幅写人物的思想感情,而且有不少场合是相当接近生活的本来面貌的。如写张生赴京求取功名,与莺莺别后在旅舍投宿:
萧索江天暮,投宿在数间茅舍。夜永愁无寐,漫咨嗟,床儿上怎宁贴!倚定个枕头儿越越的哭,哭得俏似痴呆。画橹声摇曳,水声呜咽,蝉声助凄切。(《越调·厅前柳缠令》)
活得正美满,被功名使人离缺。知他是我命薄,你缘业?比似他时再相逢也,这的般愁,兀的般闷,终做话儿说。(《蛮牌儿》)
在这里,不仅对当时张生思想感情的刻画相当细腻、生动,而且其文字也与抒情诗词的凝炼有较大差异,具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其后元杂剧的注重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走的就是这种路子。
在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西厢记诸宫调》两次写了张生的梦境:一次是张生遭到莺莺严词拒绝后,梦见她来与自己私会;另一次是张生赴京途中,梦见莺莺与红娘赶来与他相会,却又遭到五千余强徒的包围。这两个梦对情节的发展毫无作用,只不过有助于进一步显示张生的内心世界。这也正说明了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在作品中已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的意义,而不只是在叙述事件过程中处于附属地位。
第三,注重人物性格发展过程的较完整的揭示。
如上所述,作品对人物思想感情的刻画十分重视。但是,把这些刻画加在一起,并不就能较完整地显出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还必须注意其前后的联贯,使之具有严格的逻辑联系。作品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以上述莺莺在礼教与爱情的冲突中的种种表现来说,其发展的脉络就很清楚,并无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在传奇《莺莺传》中,张生要红娘传诗给莺莺,莺莺很快回了他一首,约他进去,见面后却把他数说了一顿,“张自失者久之”,“于是绝望”,但过了几夜,莺莺却自动到他的房中与他欢会了。对莺莺的这种前后相异的行动的原因,《莺莺传》毫无交代。因此,虽不能据此就说莺莺的性格前后矛盾,但至少可说作者并未注意到莺莺性格的完整性。而在《西厢记诸宫调》中,不仅对此处理的合情合理,而且把这作为莺莺在克服礼教对自己束缚的过程中的几个密切联系的阶段,进一步显示出其性格发展的可信性。在这里还应说明的是:在《西厢记诸宫调》中,莺莺在与张生私会后,其性格仍在继续发展。她与张生欢会之初,十分羞怯;但过了些时候,就显得很主动,终至成为难舍难分;于是,在张生赴京时,她变得痛苦不堪;其后崔夫人又让她与郑恒成亲,她就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这痛苦的生活了,决定自杀。像这样细腻地揭示人物性格的整个发展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
所以,《西厢记诸宫调》在中国文学史上实具有重要地位。
至于其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固然离不开辽金文学任情率真的传统,只要看其与元好问都赞美男女私情,就足以说明其间的关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从汉族长期的文学积累中吸取营养,这是只要看看作品中对唐宋诗词的大量运用就可以明白的。在这方面,既有文句的采用,也有境界的吸收。前者如表达莺莺在张生赴试后的愁绪的“非关病酒,不是伤春”(《道宫·尾》),就源于李清照的“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后者如写张生莺莺分别情景的《大石调·玉翼蝉》:“……不忍轻离别。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雨儿怎歇,向晚风如凛洌,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纵有半载恩情、千种风情何处说!”跟柳永《雨霖铃》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都说到秋日的离别更为难受,都写到蝉鸣、杨柳、雨、风,而且都以别后“纵有千种风情”无处述说作结,这许多类似之处,显然不能以“英雄所见略同”来解释。 五、宋金诸宫调 诸宫调是宋金元时流行的说唱体文学形式之一,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以说唱长篇故事,因此称为“诸宫调”或“诸般宫调”。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弹词”或“弦索”。诸宫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演唱时采取歌唱和说白相间的方式,基本上属叙事体,其中唱词有接近代言体的部分。诸宫调与前此的说唱、歌舞均有渊源关系。它继承了唐代变文韵散相间的体制,发展了以同一词调重复多遍并间以说白的鼓子词,以一诗一词交替演唱并与歌舞结合的“转踏”和集合若干同一宫调的曲调为一套曲的“唱赚”的结构。比起上述鼓子词、转踏和唱赚来,诸宫调篇幅更大,结构也更加宏传,可以表现更为复杂的内容。一方面,它既能象长篇叙事诗一样,使故事得到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它的部分唱词又兼有代言体特征,能造成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由于它交互使用具有不同宫调、声情的曲子,又为表达比较丰富的感情内容提供了条件。它是由说唱、歌舞到戏曲的演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诸宫调始于北宋。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熙宁元□间“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有“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的记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记崇宁、大观以来“京瓦伎艺”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南宋时诸宫调相当流行,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所载“诸色伎艺人”中,有“诸宫调传奇”一项,提到当时诸宫调演员有“高郎妇”等四人。同书卷十“官本杂剧段数”中有以诸宫调演唱的官本杂剧《诸宫调卦册儿》、《诸宫调霸王》二种。《梦粱录》中载南渡以后,杭城有妇女熊保保及后辈女童都善唱诸宫调,“说唱亦精”。今存诸宫调有12世纪初金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演述五代时后汉高祖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全文共12则,今存不足 5则。金章宗时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是迄今唯一保存完整的诸宫调作品。上述二种诸宫调,在创作时间上与两宋相值,所用宫调亦与宋教坊所用比较接近,表现了前期诸宫调在音乐上与宋代伎乐的承继关系。另外,元杂剧作家王伯成有《天宝遗事诸宫调》,以李隆基、杨玉环的故事为题材。今存54套曲及零星支曲,见于《雍熙乐府》、《九宫大成谱》、《太和正音谱》和《北词广正谱》中。《天宝遗事诸宫调》所用宫调、曲调以及曲子的联套方式(包括套曲长短和曲调的配合)均与元曲接近,说明了诸宫调到元代在音乐上的发展变化以及与元曲的互相影响。从现存资料看,诸宫调在北方,特别在金朝,曾有过长足的发展。宋、金诸宫调的内容颇为丰富。元人杨立斋套数〔般涉调·哨遍〕中载:“张五牛商正叔编双渐小卿”。《西厢记诸宫调》曲文中提到《崔韬逢雌虎》、《郑子遇妖狐》、《井底引银瓶》、《双女夺夫》、《离魂倩女》、《谒浆崔护》、《柳毅传书》等。元杂剧《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中提及《三国志》、《五代史》、《七国志》、《六臂哪咤》等,可以看出诸宫调内容涉及烟粉、灵怪、朴刀、杆棒、神话历史等内容,题材相当广泛。诸宫调在元代仍较流行。元代夏庭芝《青楼集》中记载杂剧演员赵真真、杨玉娥、秦玉莲、秦小莲等曾唱诸宫调。《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中表演诸宫调的艺人尚可“冲州撞府”,四处流动“作场”演出。到了元末,诸宫调逐渐趋向衰落。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载“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 诸宫调后虽衰落,它的重要的艺术手段,都为元杂剧所吸收。元杂剧的分为旦本、末本,一本由一个角色主唱到底,套曲的组织方式等,都直接受到诸宫调的影响。 七、诸宫调作品的整理 现存的诸宫调作品只有三部:《董西厢》是完整的一部,《刘知远》已残缺不全,《天宝遗事》已佚散,只剩数十套曲辞。因其数量少,故弥足珍贵。不少学者对这三部作品进行整理(校注或钩辑)。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使这三部作品得以流行于世。这里谈谈诸宫调作品的整理。 《刘知远诸宫调》一直在民间流传,鲜为文人所知,故不见于历代的稗史杂说中。直到20世纪初(1907至1908年),俄国的柯智洛夫探险队发掘黑水古城,这部被湮埋了数百年的文学珍品才重见天日。柯智洛夫的发掘规模相当大,出土的文物相当多,除了有西夏文的经卷、文书外,还有不少汉文的书籍。有刊刻于乾二十一年(公元1190)的《蕃汉合时掌中珠》,乾二十年的《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等。还有平阳(今山西临汾)姬氏刻的《四美人图》和平阳徐氏刻的《义男武安王位》两幅大型版画11 。这些出土的书籍大多都是12世纪刊刻的。据此推断,《刘知远诸宫调》也当刻于这一时期。 《刘知远诸宫调》的发现是一件具有相当文化意义的事。此前,人们只知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而《刘知远》比《董西厢》还要古老。它可帮助我们了解《董西厢》之前的诸宫调乃至民间讲唱文学的发展情况,弥补了诸宫调发展链上的重要一环。因此,引起了学术界高度的注意。不少学者对它倾注了很大的学术热情和精力,在整理和研究上获得了可观的成果。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郑振铎先生。他率先 对《刘知远诸宫调》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据郑振铎《刘知远诸宫调跋》记述,他于1930年在一位朋友(向觉明先生)那里得到《刘知远》的抄本,才知道它是诸宫调,后又见到了原书照片,只剩四十二页,内容与抄本完全相同。1957年,他到前苏联列宁格勒访问,见到了原书,确实只有四十二页。中间的将近八则,估计约有八十多页原已缺佚。“这是一个袖珍本,完全是金代(公元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年)刻本或稍后的蒙古刻本的样式。”目前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它是一部金刻本。1935年,郑振铎已将抄本整理排印,题《刘知远传(诸宫调)》,编入《世界文库》第二册。这样,《刘知远诸宫调》才开始在学术界流传。但郑本中时见文字误辨、语句错断的现象。1937年,北京来薰阁根据照片石印,题《金本诸宫调刘知远》,让人们得见该书原貌。1958年,前苏联将《刘知远诸宫调》、《聊斋图说》等一批书籍归还中国。文物出版社据此影印出版,克服了来薰阁石印描摹失真的缺憾。郑振铎的《刘知远诸宫调跋》就是为文物出版社影印本写的。到了1989年,巴蜀书社出版蓝立蓂先生的《刘知远诸宫调校注》。该书旁征博引,注释详明,对俗字、误字进行了辨析。书后列有《俗字表》,以备读者查阅。据该书的《后记》说:“这部校注稿写成于1980年。初时,曾与廖珣英先生合作搜集了一些资料,并选释了某些词语。后因廖先生另有他就,遂由我草成全稿。”廖珣英先生的《刘知远诸宫调校注》于1993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注释多有与蓝注本相同之处,而廖注本在曲调格律和押韵规则方面用功较多,其意义也是很明显的。今天容易见到的便是这两个本子。其它的整理本还有凌景埏、谢伯阳的《诸宫调两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朱平楚的《全诸宫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做了不少积极而有益的整理工作,发表了一批专门性论文。如张星逸的《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江海学刊》1964年第一期)。刘坚的《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中国语文》1964年第三期)、张星逸的《补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中国语文》1965年第五期)、蒋礼鸿的《读〈刘知远诸宫调〉》(《中国语文》1965年第六期)、陈治文《〈刘知远诸宫调〉校读》(《中国语文》1966年第三期)等。这些论文分别对《刘知远诸宫调》的刊刻年代问题、字句勘释问题、音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它的研究作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尤其是《中国语文》以系列专栏论文的形式来展开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刘知远诸宫调》的整理和研究。 《董西厢》是一部保存完整、规模宏伟的诸宫调作品,且被后世推为“北曲之祖”,董解元也为《录鬼簿》列于曲家之首,誉为“创始”(即北曲之创始)。因此,尽管明清两代的学者皆不知其为何物,但仍有不少人对它进行整理和刊印。 现存最早的《董西厢》刻本是嘉靖本。它为嘉靖年间张羽所刻,共分八卷。前有张羽的序,后有杨循吉的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燕山松溪风逸人刻本影印(1963年),题为《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赵万里等人于一九五七年在安徽绩溪县寻访到另一个刻本。它也分八卷,名之曰《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开首也有一篇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张羽的序言。卷一题有“海阳风逸散人适适子重校梓”的字样。“海阳”即安徽休宁,“适适子”不知为谁,“重校梓”即重刻张羽的校刻本。张羽,字雄飞,号黄鹄山人。他在序中说,他的校订本是以元刻本为底本。元刻本为西山汪氏所藏,张羽“借录之,然恨其手(首) 尾俱缺,舛谬殊甚”,后通过何良俊借得杨吉循所藏的抄本,才“赖以考订异同,修补遗脱,而董氏之书于是复完”。可知,《董西厢》在元代已有刻本流传,而明初至嘉靖三十六年之间尚无人刻过。 《董西厢》的重要刻本还有黄嘉惠本、闵寓五六幻本、屠隆校本(二卷)、汤显祖评本、闵齐刊本(四卷)、暖红室本(四卷)等。黄嘉惠本分上下二卷,并配有插图。卷上题有“新都杨慎点定,海阳黄嘉惠校阅”。此书的开首有黄嘉惠作的《引》。书中有清代学者王筠的题跋和批校,是一部难得而珍贵的版本。此书原藏山东省图书馆,1984年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 闵寓五六幻本是一个通行已久的版本,也分上下二卷。近人凌景埏的《董解元西厢记》校注本就是用它为底本的。凌景埏的《董解元西厢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是目前通行的版本。它以闵寓五六幻本为底,依张羽本分为八卷,“并用古本、旧钞黄嘉惠校本、屠隆校本、汤显祖评本、闵齐伋刻本、浙江图书馆藏明刻残本、暖红室翻刻闵齐本、暖红室后刻不分卷本对勘,择善而从。因《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王骥德(伯良)校注《王西厢》,引录《董西厢》词语甚多,遇上述诸本都错了的字,也有据它们来改正的。”12 该书是凌景埏去世后出版的,未竟的工作由出版者来完成。由于出版者将该书定位为普及性读物,故未出校记,对一些词语与典故只作了通俗简要的注释。除此书外,还有侯岱麟校的《西厢记诸宫调》(文学刊行社1955年出版)、傅惜华的《西厢记说唱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出版)、朱平楚的《西厢记诸宫调注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等。他们对《董西厢》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 《天宝遗事》为元代王伯成所作。该书已佚散,部分曲辞保存在明初朱权所编的《太和正音谱》、明嘉靖时郭勋所编的《雍熙乐府》、清初李玉所编的《北词广正谱》和清乾隆时周祥钰诸人所编的《九宫大成》等书中,其中以《雍熙乐府》收录最多。 郑振铎、冯沅君、任二北、赵景深等人都曾对《天宝遗事》进行过钩稽和整理,可惜未曾付梓。郑振铎曾辑得《天宝遗事》遗曲五十四套,并根据《遗事引》所述内容,将这五十多套曲子进行了排列13 ,让人了解该书的大致内容。朱禧在郑振铎整理的基础上,又对《天宝遗事》的遗曲进行了一番大集,共辑得六十套(不包括散落的单支曲子),按内容组合成七个大部分:“引辞”、“唐明皇宠幸杨玉环”、“唐明皇游月宫”、“安禄山私通杨玉环”、“安禄山被贬造反”、“马嵬坡杨玉环身亡”、“唐明皇回转长安”。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让读者能够更清楚地窥见该书的故事梗概。每套曲子后有辑者的校注。每个部分前面有提示,说明组合的理由。每个部分后面有简要的评析。书后列有四个附录:“《天宝遗事诸宫调》单支曲文”、“未找到曲文的《北词广正谱》所列《天宝遗事诸宫调》‘套数分题’”、“《天宝遗事诸宫调》残存套数索引”、“有疑议的作品”,为诸宫调研究者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朱禧所辑的《天宝遗事诸宫调》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是目前较为通行的本子。另外,凌景埏、谢伯阳的《诸宫调两种》,在赵景深的帮助下,也辑得遗曲六十套、零曲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