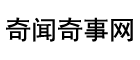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注一)。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落于东院,寺之规模,更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帷阁及山门。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第二十三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其构架约略可分为三大部分:柱,斗拱,及梁枋。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第二十六图),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阱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各不同(注二),条理井然。各攒斗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才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注三)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梁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
阁与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物,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般。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重朔,尚具唐风,其两傍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此二者俱属事实,亦只为寺创建之时,或其历史中之一段。至于今日尚存之观音阁及山门,则绝非唐构也。
蓟人又谓:独乐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亦禄山所命,盖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尔命名云。蓟城西北,有独乐水,为境内名川之一,不知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为禄山命名也。
独乐寺观音阁
独乐寺观音阁
独乐寺观音阁
独乐寺观音阁
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