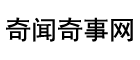1899年至中国游历,著《燕山楚水》。
1907年10月被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两年后升为教授,讲授东洋史。
1909年11月从住北京的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京师大学堂的罗振玉处,得到伯希和在北京展示敦煌写本的消息和部分照片,立刻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续发表《敦煌石室发现物》、《敦煌发掘的古书》,首次向日本学界介绍敦煌文书的发现及其价值。
1910年8月又在《朝日新闻》上发表《西本愿寺的发掘物》,介绍大谷探险队的收获,并应邀参加大谷收集品的整理,编辑《西域考古图谱》(1915)。在获知中国官府已将藏经洞所剩文书全部运抵北京后,与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冈谦藏、滨田耕作奉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之命,于1910年8月至11月到北京调查敦煌文书。翌年写出《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并将所获资料展览。
1924年,率弟子石滨纯太郎往巴黎、柏林等地收集资料,归国后发表《欧洲所见东方学材料》。
支那学派日本东洋史学已独立发展,不能等同于汉学或中国学,最早提倡者为那珂通世于高等中学的教师会上。而在各大学东洋史学科的成立中,首倡者那珂通世虽在东京大学,但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的成立尚晚于京都大学。
在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三讲座中,又因讲座教授者受训背景的差异,因而在京都大学形成两种不同研究理念的学风。即以内藤为首的“支那学派”,及以桑原骘藏为首的东京学风。
表现在京都大学的两种不同学风,实即日本东洋史研究观点的缩影,亦即表现于京都大学内的东洋史研究风尚,有“支那学派”与“东洋史学派”之分。两派的中国史观,分别是“东京学派”采极端否定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即以德国兰克学派为史观;而“支那学派”的中国史观则是极为推崇中国文化,且与中国学者保持良好的往来关系,三田村泰助喻之为“内藤学”,亦是所谓“京都学派”的主导奠基者。
两派主要的歧异,在于对中国考古文物的看法,东京学派以甲骨等考古文物为伪物,而内藤等“支那学派”则视其可证之史实。
但此种对立的中国史观,并未影响两派学者间的私谊。持此种对立史观的学者,亦被后来的学者以对比的方式进行研究,如增渊龙夫的研究,即以内藤虎次郎与津田左右吉为对比,研究成其大作。继其后者,尚有五井直弘等人。
两大学派虽史观不同,但都不可免的,参与了日本为侵略亚洲大陆所设立的研究事业。或因此,被讥为为帝国主义者服务。又由青江舜二郎及竹田笃司二氏的回顾,可窥知当时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学科的声望,更在东京大学之上。然此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所在,仅作为时代背景的了解,主要还是在探讨内藤史学研究方法,及其学术观点。
历史发展学观内藤的历史发展观中,影响较大的有“天运螺旋说”与“文化中心移动说”。前者,有喻之为“天运螺旋循环说”,亦有学者视为大势论或时势论,然其间应有些微的差异。内藤此说的提出,即在反驳欧西学者的“中国文明停滞说”,即内藤有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史观,但其认为历史变迁虽是循环的,然其发展过程则是有差异的。
此外,内藤期望“天运螺旋循环说”的应用范围需加以扩大,期达于真、善、美之境,如此可得有一大有作用的学理。另一历史发展观即是“文化中心移动说”,内藤以文化中心的移动促成了统一大势,即其文化中心的移动非相对的兴衰,乃是文明的普及,即文化中心移到哪儿,文明即被带到那儿。即文明所到之处,该地即得到开发,开发的成果当会使文化差异缩小,因此而带来统一的气运。或因此种史观,内藤看中国五代的割据,不仅未妨害文化的发展,反而有助长文化的普及。
又其“文化中心移动说”,早已应用在其第一本著作《近世文学史论》中,可知此一史学研究理论,与其学术研究相伴随,可视为其史学研究通则之一。此外,即其在“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历史观中,表现其对边陲文化的注目。
因此,其以汉代的发展受秦、楚文化的影响。就内藤所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交流,而每一种文化交流必当汇流产生出自有的特色。因文化交流是缔结人类文明的重要元素,笔者深信所有灿烂的文明都是经此文化交流的过程而来。
内藤湖南